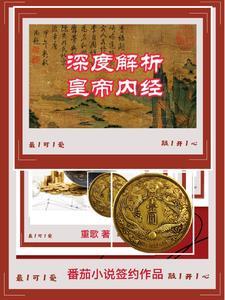布丁阅读>狼夫啸月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皇帝只要想到那些西域女子,想到她们如水蛇般的曼妙身姿,以及具有西域特色的绝美容颜,他瞬间浑身燥热起来,哪怕已过了寻欢的年纪,也忍不住冲动着。
李公公颔首应了句‘诺’,然后着手派人去打探西域舞姬的消息。
易太傅这次病得不重,卧床两日就恢复了往日的精气神,他知道茗月是个倔性子,又碍于狼王是她的救命恩人,所以并没有立马将他赶走。
但是毕竟男女有别,茗月日后还得嫁人,与外男走得亲近已经是有悖女德了,若真让他住在女子的闺房中,那岂不是乱套了么?
于是,他以宾客之礼款待狼王,将他安顿在易府内上等的庭院厢房中,并配以婢女小厮在旁伺候。
狼王被府里的一位婢女带到厢房里休息,婢女有些畏惧他,一直不敢与他走得太近,进屋后便对他说:“侠士请自便,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婢子就先行告退了。”
“慢着!孤有事要问你。”
婢女难掩惶色,但又不敢怠慢,于是小声应道:“侠士请说。”
“月儿住的屋子在哪儿?”
狼王环顾四周,这偌大的府邸足有他那山洞的数倍大,里边又错落着大大小小的院子和屋子,他想见茗月,却又不熟识易府的路。
“侠士若是想见女公子,直接吩咐婢子就行。”
婢女躬身退至屋外,回到庭院西侧的小房中,离宾客的厢房只有几步之遥,所以专门供那些伺候人的婢女们住。
狼王平时习惯了风餐露宿,对他而言只要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屋檐就够了,更用不着派人伺候他。
待婢女走后,他悄悄离开厢房,自个儿循着来时的记忆去找茗月住的地方。
儿时的他曾被茗月带回易府,但他的记忆里只有那间被填满一堆捆柴的狭窄屋子,门一关,里边便是暗不见天日。
他鲜少被带出那间屋子,就算是被放出来,也只能是在深夜,然而他在易府里去过的地方不多,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易府也变了样儿,这座府邸对他来说又是陌生之地。
“谁人在那儿?”
狼王越过庭院长廊时,听见后头有喊声,他回头一看,来人竟是茗月的继母丁氏。
天色暗,丁氏似乎没看清他的模样,还以为是府里的小厮,远远地就对他说:“不好好伺候主子,在这儿瞎晃悠作甚?当心管家扣你月钱!”
狼王虽不懂丁氏所言何意,但丁氏那责骂的语气令他尤为不快,他堂堂狼群之首还要听一个柔弱妇人指挥?
若是按照以往,他一定是上前揪住妇人的衣襟教训一番,但他一想到茗月嘱咐过行事莫冲动,于是他忍了。
狼王不予理睬,自顾自地往前走,继续往茗月所居住的院子走去。
哪知那妇人不知好歹,责骂声越来越大,“你这混账小厮,竟敢无视本夫人?你给我站住!本夫人倒要瞧瞧是哪个胆大妄为的混账东西,明日个就将你遣出易府!”
我不许你们杀他!
丁氏迈着碎步,疾冲至狼王身后,正欲像往日教训小厮那般揪住他的耳朵。
警惕的狼王即便是背对着她,也能察觉到身后之人的动静,他只是稍微侧身躲避身后人的攻击。
却不料丁氏因为心急,走得快,没来得及停下脚步,与他的左肩擦肩而过,然后不慎撞向长廊边的朱红梁柱。
“哎呀!你这混账小厮竟想害我?”
丁氏转头之际瞥见了狼王那张不可一世的脸,她顿时间傻眼了,呼救的话还没说出口,恁是被咽回了肚中。
“是你?”
碰见他,她自认倒霉,但心里头憋着气却难受得很,她质问狼王:“这深更半夜的不好好待在房里歇息,出来闲晃作甚?”
“哼!”
狼王不屑解释,更不想再见到丁氏那张两人憎恶的面孔,他冷眼瞪了她一眼便转身离开。
丁氏受了气本就不好受,又见他这副藐视人的态度,身为太傅府女主人的她不容许府里留有这样的野蛮人。
她回屋后在太傅面前委屈落泪,将狼王如何对她无礼,又是如何害她受伤的事哭诉给易太傅听。
护妻心切的易太傅见她捂着额头不敢见人的样子,他急忙问道:“夫人这是伤着哪儿了?为夫这就给你请大夫。”
“夫君有心思给妾身请大夫,倒不如好好琢磨着怎么赶走那个蛮不讲理的野人吧!”
“这可人家毕竟是救了月儿一命的侠士,老夫岂能无情地赶他走呢?”
丁氏指着额间被撞红的伤痕,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他,“月儿的命是命,妾身的命就不是命了?”
“可可是”,易太傅也为难,请神容易送神难,况且狼王又是个横行霸道之人,稍有不满意,他的狼群就会出现,就怕到时候再度引起骚乱恐慌。
丁氏掩面叹息,她自己又何曾不畏惧这名陌生的男子?
说起狼的事,她蓦然回想起十年前的往事。
“不知夫君是否还记得十年前茗月曾经带回来的那个狼孩?妾身总觉得这个自称‘狼王’的男子和当年的叛逆狼孩有几分相似。”
易太傅听闻此话后愕然一惊,他急忙做出嘘声的手势,“当年的往事不可再提!如今的月儿已经不记得那个孩子了,咱们就当他从未出现过,否则老夫不敢想象月儿记起那段记忆后的样子。”
丁氏的话让他也逐渐怀疑起狼王的身份,易庄只要想起当年的事,心里头便感到惴惴不安,夜里服下安神药才能勉强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