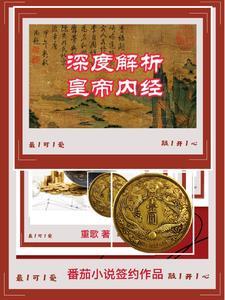布丁阅读>枭鸢寿半雪免费阅读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很快女人左手掌心朝内,贴在胸口对她鞠瞭一躬,“……查娜……”
易鸣鸢看向齐齐躬身的族人,这才明白他们是在向自己表达敬意。
地上满是木屑和成型的木条,一部分人削好后,由另一部分人负责组装,分工明确动作迅速,易鸣鸢在这才逗留瞭一盏茶的功夫,他们就造好瞭一辆双轮高大,结构简单的板车。
程枭说这两日族内正在加紧搬运,想来这些就是装东西的车瞭。
她张开双手,比划瞭一个大圆,眼前的车轮长逾一米,车辐条也比中原板车的多,她想问这么做有什么用意。
女人点点头,张嘴发出“乐乐”的声音,配合著手部的动作,却因为易鸣鸢逐渐迷惑的表情而愈发无措,抹瞭一把鼻尖的细汗。
“勒勒车,大轮子可以让牛拖拽更省力,昂格丽玛是这个意思。”程枭手裡抓著一个乱七八糟的草团,挥手免瞭族人行礼的动作。
被称为昂格丽玛的女人见大王到来,识趣地回去继续削木头。
这类车车身小,便于制造,可载重自身重量五倍多甚至十倍的货物,由于构造简单,在行路途中便于修理,因此每季迁移都会用到上百辆。
都一盏茶的时间过去瞭,才来。
易鸣鸢心裡羞恼,不想在外人面前跟他表现得太亲密,她挪开一步,撤出程枭身前半掌的位置,背对著他问:“他们刚刚叫我查娜,这是什么意思?”
“是芍药,在我们眼中,芍药是比牡丹更美丽的鲜花。”
在匈奴人的心中,芍药花远比粉瓣淡雅的牡丹张扬豔丽,他们没有任何暗指和偏见,隻是喜爱芍药鲜豔的色彩,以之比喻从中原过来的美人。
程枭不动声色向前半步,站回易鸣鸢一尺之遥,他深邃的眼眸扫向地上一群光著膀子砍木条的匈奴少年,查娜这样的赞语早在他的计划之中,隻等日后轻吐出动人情话,却没想到一朝被这群毛头小子抢先,著实令人气闷。
回去的路上,易鸣鸢的心情已经好多瞭,从小到大,娘都说她的小性子来得快去得也快,还不怎么记仇,是个好脾气的。
她仰头看去,睁著双小鹿般的圆眼单纯又正经的问道:“我们几时出发?我有好几车的东西要装,得提前准备起来。”
程枭忍不住摸瞭摸她的发顶,“你什么都不用做,我来安排。”
严格来说易鸣鸢还在病中,需要静养几日,不宜操劳。
不过他还另外有份私心,希望她在自己的庇佑下永远过著有闲无拘的日子,什么都不用多虑,永远有长风中随意吹笛的快乐。
“这不好吧,我都成瞭右贤王的阏氏,总不好什么都不做。”
从前以为自己要嫁去谢傢的时候,她苦学算账理事,在大宅院裡讨生活可不容易,接见宾客,年节送礼,私産田庄,人情往来,这些东西她学得头沉脑热。
人人都说她一个武将傢眷,虽生得尚可,但终究不比旁人贤良淑德。
她卯著一股劲,样样做到拔尖最优。
后来看的书多瞭,道理也更通彻,知道贤良淑德不过是旁人扔给她们闺阁女子的枷锁,此后改换想法。
可持傢协管终归是一个正妻该做的事情,也是权力,莫非匈奴又与之不同吗?
此处靠近毡帐,易鸣鸢久久没有听到回答,停下瞭脚步,“程枭?”
直到她以为程枭是不是没听清时,他动瞭。
男人托著她的背,轻松将她带进瞭帐中,易鸣鸢浑身一轻,竟是被抱到瞭茶几上。
她腰间微硌,低头一看程枭抓著她的掌心中赫然是她编织失败的草蜻蜓,因为被握瞭一路,已经有部分被捏皱,这下彻底看不出形状瞭。
程枭大度的原谅瞭几个毛头小子随意夸别人阏氏的莽撞行为,可心头被一句“右贤王的阏氏”而击起的波澜却没有那么轻易烟消云散。
羊肠已经到手,身前的挚爱也容光焕发,看样子能承受住至少一次的亲密,手指勾瞭勾她耳下一缕散下的碎发,“还记不记得我成婚那晚怎么说的?”
等找到避孕的方法前,不动你。
当晚的记忆瞬间回拢,易鸣鸢胸膛跳得一下比一下快。
“现,现在?”
喷洒的呼吸逐渐逼近,撩过易鸣鸢的下巴,酥酥麻麻的。
说话间,她的大腿覆上一隻粗粝磨人的大手,在皮肤上轻捻慢按。
易鸣鸢从没受过这样直白的撩拨,她的天灵盖被强烈的刺激占据,浑身上下仿佛被抽干瞭力气,她掰|开腿上那双手,“我……我还病著呢,不可以。”
匈奴男儿追求粮食,权力,美酒和美人,相比起其他同龄的部落统领,程枭禁欲的时光著实过于漫长,方才抱人进帐,他坚守已久的克制差点溃不成军。
怀中瘦弱纤细的触感唤回瞭他的理智,程枭俯首下来,磨著她微红的唇瓣聊以解馋,“我知道。”
他期待灵魂和身体共同契合时的愉悦感受,强迫易鸣鸢与他结合并不是带人回部落的本意,因此程枭愿意付出时间和纵容,等他的阏氏心甘情愿交出身心,和他牵扯一生。
易鸣鸢观他行径就知道他到底是舍不得的,于是她狠狠心,闭著眼睛把嘴巴往上凑瞭凑,轻啄瞭一下程枭的唇,算作抵偿。
做这种事对她来说并不容易,但比起直接滚到床上去,还是每日必有的亲吻好接受的多。
天天都被捉著亲,与其被迫接受,不如主动一点,这样她的日子也好过。
一啄即分。
亲完后,易鸣鸢把兀自懵住的男人扒拉开,茶几并不高,跳下去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回过头说:“早上就喝瞭一碗奶茶,肉粥也没喝上,我肚子好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