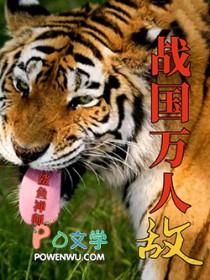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站(zan)起来 > 第124章(第1页)
第124章(第1页)
“他向来如此。”嵇暮幽抿了一口碎茶,淡然道:“余将军放他去做,做成了,是你主将之功,若败了,再罚不迟。”
余元开深觉有理,回座吃了两口茶,踌躇片刻问:“此前靖王殿下和章仇将军感情甚笃,怎么如今却有了嫌隙?”
“啧。”嵇暮幽莞尔,“余将军好天真,人之相处,以利结合。此前在京,他能助我,而在这边服之地,自然是余将军更有倚仗。”
这荒漠边塞待了许久,余元开还是头一次感到春风拂面,飘飘然面上嫣红,立刻躬身示好,“靖王殿下如此这般看重,末将定……定不负所望……”言毕要上前挨着嵇暮幽,却被嵇暮幽用脚尖顶着肩膀推开,他直呼自己唐突,满面桃花地嗤嗤地笑。
再说章仇阎,他登高看清了形势,指了亲信的一队从西抵御,自己纵步上马,迎战东面敌军。
赫兰人善骑射,此番围攻便是骑兵打头阵。赫兰中心城街道宽广,骑兵并不受限,打得余元开的士兵节节败退,离营门也不过一射之地。
章仇阎夹紧马腹,挥刀斩敌,杀出血路。他方才看得清楚,以此次赫兰叛军的兵力布局绝不是余元开轻描淡写的试探,而是真切地想要拿下中心城。守军军纪涣散,训练松弛,已然溃不成军,自己麾下的这支骑兵尚未到最佳战力,人数也有限,速战速决乃是唯一选择。
此番混战若要速战速决,唯有取敌将首级!
章仇阎左劈右砍,蹄疾风啸之中锁定敌军将领,高喝一声,提起缰绳冲上前去。
赫兰将领自认不虚,待到章仇阎进到眼前,才心生不安——只见章仇阎眉目闪现血光,信手甩开刀刃血珠,如恶鬼食人一般盯紧了他。“阎罗”二字闪现在脑海,原来这称谓如此熨帖,那赫兰将领稳住自己莫名颤抖的手腕,将剑刃对准了来人……
鸦啼阵阵,空气中弥散着铁锈的甜腥气味,章仇阎以一敌百杀退了敌军,带着残余部队回到营帐。
“章仇兄弟真是名不虚传!”余元开谄笑迎上前。
章仇阎却不看他,径直将一颗头颅甩在案上。
余元开与那有着熟悉面庞的头颅的未合双眼恰好对视,不由冷汗涔涔。
“末将现在令人去清扫战场……”与其说是请示倒不如说是通牒,余元开忙不迭指了两个人去帮忙。
直到章仇阎的身影消失,余元开才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慌乱地让亲卫把那晦气的脏物拿走。
亲卫士兵一拥而上,都想争功,却不想血液滑腻,不知是谁手一滑,竟任由那头颅滚到地上,散乱发丝间的浑浊双目,空洞地对着余元开,余元开双腿打颤,险些憋不住尿了一地。
嵇暮幽默坐打量余元开的异常,认定这颗刚离开躯干不久的赫兰人头颅与这胖子有些交集,他暗道有趣,面上仍是淡淡的笑意,“余将军快写信回京述职吧,别忘了替我美言几句。”不及余元开回答,兀自离开。
战场清扫直至深夜,因离营帐太近,埋坑焚尸都得格外仔细,稍不留神就可能留下疫病的祸根。星河低垂,章仇阎任由马儿信步,最终停在半塌的古城墙边。
“今日这仗打得漂亮。”
章仇阎循声抬眸,见自城墙之上悬下一条腿,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晃荡。章仇阎放马儿去嚼荒草,自己拾阶而上。
“依你所见,余胖子带的兵战力几成?”嵇暮幽横在城墙上,枕着手臂望天。
“不堪一击。”
“这么弱的一支队伍却安稳守了几个月,实在蹊跷。”
章仇阎看向嵇暮幽,他知道嵇暮幽和他有一样的猜测。
“城中百姓如何?”嵇暮幽又问。
“眼色极高,已自行撤离。”
“唔。”嵇暮幽沉吟,坐起身,从袖中拿出密信递给章仇阎。章仇阎看罢,眉头紧蹙,“皇后临盆之期将近,一切都要从速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弄清余元开和赫兰叛军之间到底有什么勾当。”嵇暮幽揉了揉眉心,一想到那一要紧时间元小萌可能遭遇不测就不住烦躁,恨不能飞回京城,孩子气般地愤愤道:“可我在这守了一夜,一匹狼都没看见。”
“这倒不必担心。”章仇阎说罢,掌间垂落一枚狼牙。
“哪儿来的。”嵇暮幽借着月光眯眼细看。
“今日那个赫兰将领项上所挂。”
“倒是意外之喜。”
-
十余日后,此战战报快马加鞭送抵京城。
“赫兰军发动奇袭,余将军运筹帷幄方守住营地,不失寸土。”
“青-天-白-日,算哪门子奇袭?”嵇暄然蔑然一瞥,叫一群大臣相顾无言。
“知余将军一人守城艰难,便派了章仇家的去,最精良的骑兵如今却打了这么不尴不尬的一仗,也好意思上奏请功。”嵇暄然将战报丢在案上,底下登时跪倒一片。
“皇上息怒,章仇将军许是初到赫兰州,尚不习惯。”
“正是。赫兰州气候异于中原,想来马疲人倦也未可知。”
“且章仇将军赋闲在家多年,总得需时日历练。”
嵇暄然无奈长叹一口气,“他若有他父亲一半,也叫朕少操些心。”
众臣无言,只听得刻漏滴答。
“皇上,有急奏。”
嵇暄然抬手,便有一内侍快步上前附耳低语。众臣竖起耳朵,也未能听得片语,只见年轻的帝王额角蓦地突跳。
少顷,章仇蛮匆匆入宫。
“这个时间你非召前来,还能指望皇上马上见你?”总管拉住莽撞的章仇蛮道:“前些日子你为了兄长冒犯了皇上被禁足一月,这才刚解禁,何故又来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