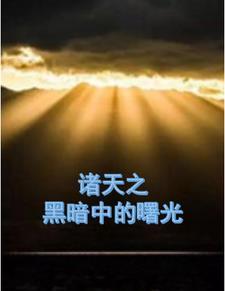布丁阅读>长安夜雨翻译及原文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父皇甚少叫她的封号,青罗心下一紧,强自镇定,只装作未懂他言下之意,气愤道:“大理寺无故扣押儿臣的护卫,全未将儿臣放在眼里,甚是气人,父皇还想偏袒大理寺么?儿臣不服!”
皇帝皱起眉,沉默半晌,问:“此人如何做了你府上的护卫?”
青罗十指握紧,斟酌道:“她兄长酿的酒好,儿臣曾与他买过酒,后来见她有些功夫,人又伶俐,还是个小娘子,稀奇得紧,便收在府里了。”
皇帝探究地望着她,“你为何不告诉朕,而是去鸣鼓?”
“登闻鼓不正是用于鸣冤么?”
青罗理所当然地反问了一句,继续道,“幼时路过丹雀门,母妃曾与儿臣说,登闻鼓乃是父皇专为蒙冤者所设,但凡有冤,便可击打此鼓,今日儿臣去过大理寺,便知那护卫蒙了奇冤,她是儿臣的人,她蒙冤,便是儿臣蒙冤,儿臣便想着敲登闻鼓,请父皇为儿臣伸冤。”
说到此处,已有些气竭。
皇帝又问:“你去大理寺要人了?”
青罗嗯了一声,“他们竟不理会儿臣!”
皇帝斥道:“胡闹!”
青罗索性胡闹:“大理寺欺负儿臣,父皇若不办他们,儿臣颜面何存?”
皇帝凝眸望着她,久久未语,大抵是将她看作了顽劣又愚蠢的孩童。
末了终是叹了口气,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命中书舍人拟诏,想想又道,宣翰林学士。
众臣鱼贯而出,殿内空阔,秋光入室,一地清幽。
皇帝瞥她一眼,似是才留意到青罗颊上的血痕。
青罗在他眼中分辨出几分厌恶,忽又想起前世他逃离长安那晚,对陈丽嫔提起她时的漠然。
“叫驸马送你回府吧。”
青罗脱口而出,“不要,”见皇帝莫名地看着她,忙又放低嗓音道,“儿臣不要他送。”
皇帝不知想到什么,别开眼,也没勉强。
青罗走出殿外,轻轻吁出一口气,仰面望天。
仍是方才那一片灰沉的天幕,云气又似淡了些。
王栖恩担忧地望着她,“殿下可还撑得住?”
青罗摇头,说没事,一张脸却苍白得血色尽失,如经风雨摧折的瘦花,摇摇欲坠。
谢治尘自廊檐尽头走来,原还低头与身旁宫人交代什么,待看见她,又瞧出她不对劲,脸色便是一沉,大步朝她走来。
青罗自知此刻模样骇人,原想就走,谢治尘却已到了跟前,只得勉强牵起唇角,朝他一笑:“驸马来了。”
谢治尘脸色紧绷,未作声,抬起手,想去触碰她受伤的面颊,近至眼前,又停下,屈起手指,转而向上,以手背贴了贴她的额头。
青罗退开半步,垂眸道:“本宫没事,大人去忙吧。”
谢治尘将手中的卷册交给随行宫人,这才留意到青罗身后的王栖恩。
王栖恩与他耳语几句,不知说些什么,他低头听着,幽深的双眸安静地锁住她。
“谢某去去就回。”
他对王栖恩微微颔首,走回来,弯腰将她横抱在胸前,转身,拾级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