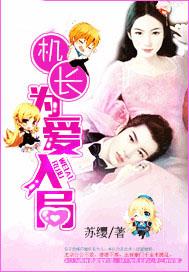布丁阅读>唐朝一书生 > 第13章 当歌伎(第1页)
第13章 当歌伎(第1页)
县衙,刑房。
一老吏捧着册子而来,满脸堆笑,语气中带着几分讨好:“小公子,这便是《唐律疏议》。”
“多谢先生。”李佑双手接过,眼中满是好奇。
老吏连忙摆手,赔笑道:“不敢当,不敢当。”
李佑这些时日闲散衙中,殊觉无趣,便想着找本律法之书看看。一者消磨辰光,二者习认繁体字,三者通晓唐律,以为日后筹谋。
衙中胥吏皆不知其根底,或疑为苏氏远亲,或猜系崔令故旧,故皆容他自在穿堂过户。李佑亦乐得借势而行,权作闲云野鹤。
至若苏家书僮之议,尚未与小妹萱娘相商。然彼心知,萱娘素来唯兄命是从,必答"但凭二兄作主"
其实李佑心里琢磨着,做家奴也并非不能接受,只要不被刁难虐待就好。毕竟自己和小妹如今无依无靠,再过个把月,冬季就要到了。
唐末这世道本就艰难,北方的冬天更是难熬,要是小妹再生病发烧,可就麻烦了。而且他想着,只要自己能平安长大,往后还怕没机会离开吗?
至于什么大唐皇室身份?开什么玩笑?都不知道多少代了,有没有写进族谱,别人认不认还是个问题。
况且如今这大唐,局势动荡不安,说不定日后还能寻个机会干出一番大事业。要是真到了改朝换代之时,在那新朝统治下做个普通百姓,李佑自觉也没那安稳度日的命。
若是形势所迫,少不得要抗争一番,意可学一下昭烈帝,佑乃太宗皇帝之后,成功了自是最好,若失败了,大不了带着小妹远走他乡,或者找个寺庙出家。
他之所以没立刻答应苏皓,就是想着等崔洋回来,看看这位知县大人能不能给出更好的条件。
……
李佑坐在刑房里,小心翼翼地翻开《唐律疏议》。
开篇是对律法的详细阐释,紧接着便是关于家族伦理、丧葬祭祀等方面的规定。
其中丧礼讲究五服之制,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根据亲疏关系不同,丧服的样式和守丧的规矩都有严格区别。
李佑读起来,连蒙带猜倒也能明白个大概,但还是有些生僻术语不太理解,便向刑房老吏请教:“先生,继母、养母、嫡母、生母、庶母,这些我都能领会,可这‘慈母’又指的是哪位呢?”
老吏捋了捋胡须,耐心解释道:“若嫡母或生母早亡,孩童由父亲的妾室抚育成人,那这妾室便是此子的慈母。”
“原来如此。”李佑恍然大悟,不禁感叹这律法中的门道还真不少,很多司法用词和日常俗语大不相同,确实需要行家指点。
李佑接着往下读,当看到关于刑罚的部分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唐律的刑罚种类繁多,且极为严苛。像什么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那刑罚之严酷自不必说。就连一些寻常的犯罪行为,处罚也相当重。
比如斗殴致人重伤,根据情节轻重,可能会被处以徒刑甚至死刑;若是盗窃,除了追回赃物,还要根据盗窃数额和情节施以笞刑、杖刑,重者可能被流放。
李佑继续翻看着,又看到关于家族伦理犯罪的条文,不禁皱起了眉头。若子孙咒骂、殴打长辈(父慈子孝),那可是大罪,要受到严厉惩处;兄弟之间若是为了争夺家产而互相伤害,同样也要被治罪。
李佑忍不住询问老吏:“先生,这兄弟间因家产起纷争,真会被如此重罚吗?”
老吏苦笑着说:“律法虽严,但也得看实际情况。前年城东陈记布庄,兄弟俩为三间铺面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哥哥挨了二十脊杖,弟弟发配三百里。
若是寒门小户,倒能劝和了事。可要是高门大族——"那官府自然会依法处置。毕竟这律法是维护世道安稳的根本,不能轻易废弛。”
李佑点了点头,继续研读。这一看,才发现这《唐律疏议》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从官员的职守到百姓的日常行为,从田产交易到婚姻嫁娶,几乎无所不包。
白天在刑房,李佑只看完了几篇。天色渐晚,他抱着这本《唐律疏议》,准备拿回县衙内宅接着看。临走前,他突然想起苏皓提的书童之事,便向老吏问道:“先生,我想问问,那义男(奴仆)入的是什么户籍呢?”
老吏微微一愣,随后详细解释道:“户籍分主户和附户。与主人同住的义男,附籍在主家主户之下,视同主家的晚辈;若有自己的田产且分开居住的义男,则单独落籍为附户,地位与主家雇佣的帮工类似。另外,若是收养义男、义女时间不长,也按帮工来算。”
李佑又问:“那何为帮工呢?”
老吏叹了口气说:“这帮工啊,身份有些尴尬。在雇佣期间,他们地位低下,如同奴仆,要听从主家的差遣,甚至连家奴都能使唤他们;但若是雇佣期满,他们便可恢复自由身,子孙也能参加科举。”
李佑这才明白,原来这唐代的帮工和自己原本理解的不太一样,民间都称其为“雇仆”,和普通的短工、长工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帮工地位不高,常受主家苛待,但好歹还有个盼头,不用改姓氏,子孙也有出头之日。
“多谢先生赐教。”李佑拱手谢过老吏,怀揣着满腹心思,朝县衙内宅走去。
……
崔洋终于回到了县城,但整日忙得脚不沾地,很少回县衙。
他这次可真是胆大包天,竟将征收上来的秋粮全部扣下,拒不送往郑州府上交。而是把这些钱粮全都用来赈济新郑县的灾民,还上疏朝廷,恳请皇帝减免赋税。
这赋税不上交,政绩考核肯定过不了关,崔洋这是拿自己的仕途在赌,只为拯救万千灾民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