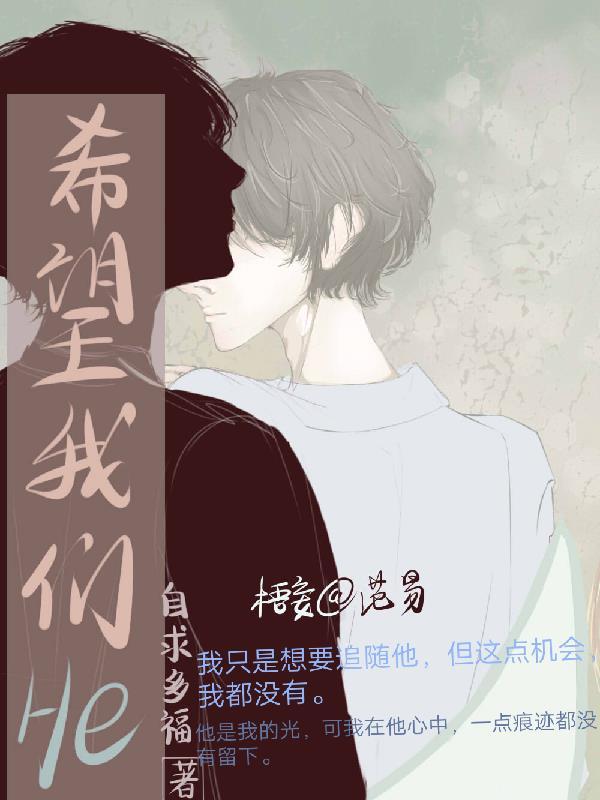布丁阅读>明月 刀客 > 第13章 手指(第1页)
第13章 手指(第1页)
秦于方回来后面色不大好,身体僵硬,。
居成阳有些不解,歪头看了他半天,嘶了一声,抱着膀子问道。“有人阻拦你查案?”
秦于方抿了唇,没说实话。“不是,官子成家来人。”
官差停了全程一撇嘴,不说被逼着和离的事,是怕居小姐很开心地落井下石吧。
“那你脸色很难看哦。”居成阳信了。
秦于方将茶壶里的水在肚子里倒了个干净,抱怨道。“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什么规章制度都一定要触犯一下,哪里来那么多无关紧要的通融。”
居成阳伏在桌上写了几行字。“你让人悄悄地把这个东西送到我父亲那,有人来试探你了,人的手段防不住,以防万一,我们早做准备,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
秦于方看了两眼,没什么敏感字眼,点头。
官差接了也小声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官子成平常就习惯干一点出格的事,彰显一下自己的特别,说他就小题大做,不说就膈应人。”
居成阳抱着一丝也不放过的心态:“他都干什么?”
“那倒没什么,就是总半夜要点酒,吃点点心。”
秦于方嗤笑一声,坐下拍了拍放证据的盒子:“还真拿自己是个爷了,接着供应,但是都要记下来。”
“属下明白的。”
秦于方又问居成阳道:“你在这还发现什么了?”
他将东西带走了,居成阳没有东西能研究。
干嘛?居成阳面露嫌弃,义务打工,当然要在眼皮子底下干,什么积极的人物,还自己争先恐后地上了。“没有,在睡觉,顺便问了几个人门口的人晚上的情形,人都在各自的屋子里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衣服我也查了,没有洗的痕迹,也没有烧,没有血衣。”
他们没指望有什么一目了然的证据。
秦于方起身。“那我先看看后面的东西。”
上次已经将纱和布的东西翻过,书架也弄过。
这次将烛台花瓶,窗台等地方又细细地搜了。
居成阳走过时把卷好的帘子碰了下来,听到声音下意识去抓,却发现有些轻,在网上抓了两个,依旧如此,再往上却是实心的。
拿了把小锤子轻轻砸开。
果然有东西,第一个是一张纸,被保存得极好。居成阳道。“我找到了一样东西。”
“定亲书?是姚坚的。”秦于方接过,辨别了一下纸张和书写的大概时间。
居成阳又将上一个砸开,是一份血书,轻轻抖开碎末。“定亲书上的名字就是姚坚嫖妓的那个女子。”
“这也有记载?!”秦于方吓了一跳。
居成阳无语。“这份血书里的名字就是沈妤!”
“将军因我蒙羞,却频频遣人护佑,此心今生难报,父母逼我自尽,是为钉死将军罪状,我若能逃出定然要为将军翻案,只盼君日后事事顺遂,沈妤留。”
居成阳有些惋惜:“没有她的其他信息附上应该是被逼死了。”
秦于方却想到了这女子若是活着以后的状态该是如何。“平民女子,没了丈夫,没了名声,若是旁的还便罢了,可偏偏是被卖到青楼过,纵然有人知道其中内情不介意,流言蜚语跟着一辈子,男子三心二意是常有的事,若是人品有瑕,不能好聚好散,这便会成为一把最锋利的刀,日后官途不顺,日后与父母决裂离心,一切一切都会怪罪到她的身上。可这女子却是最无辜的一个棋子,我遇到过许多这样的案子。”人心易变最是可怕。
“那就不嫁,自梳女有的是,说得好像死了是她最好的归宿似的。”居成阳就瞧不上那些立不起来的人。
“总要接受有很多人是软弱的。”
秦于方说到底这样的悲观其实也是因为他知道的只有过得不好的而已,也许世人都因此被蒙骗,才将白绫一遍一遍缠于自身。
再往上敲一个是一张卖身契,居成阳:“同兴十四年,姚坚是同兴十五年充军,这是更早一些的。”
秦于方凑过来瞧。“可是她又怎么会变成妓?这收钱的人也姓沈,是他父亲?”
“信上说父母相逼,应该是他父亲卖的,同什么人合谋,姚坚将军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有前程,沈妤家是个平民百姓,算是良配,她父亲若是想攀附权贵,这也算是最好的选择,可是那也大可不必把女儿卖进青楼。”居成阳的脸色也不是很好。“有没有可能她是同姚坚将军在一起的当天被父亲偷卖进青楼,被算计了?”
“有可能啊。”若是没有破绽,就造破绽,时间差,巧妙可行。
居成阳再去帘子上找,里头却都是实心儿了。“这还能证明是被算计了吗?”
“她父亲算计他女儿和女婿做什么必然是有利驱使,那血书中也说,是有人给了他父亲的好处。”秦于方问。“姚坚又与谁有仇呢?”
居成阳低下头整理碎了的渣。“吴将军也许会知道。”
秦于方扫了两眼这不大的屋子,却有这么大的秘密:“金云的这些证据藏得真是够深,几乎难以让人知道这是来翻案的,甚至换了一个人的话,草草抓一个足以交差的人,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