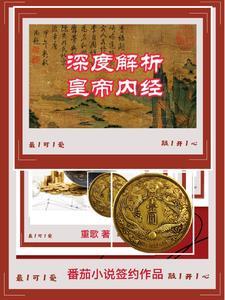布丁阅读>七爷为何这样+番外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看官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吴先生悠然地闭起眼睛,捋髯沉吟,不开口说一个字。
“吴先生!”那名送女儿红的看官气呼呼道,“您再不开口,我就将女儿红带走了。”
说着,抱起女儿红要走。
闻言,吴先生眼睛未睁,嘴角一开,先做声:“诶,少年啊,别冲动别冲动,我方才是在酝酿。今日天凉快,我坐着说,看官们也坐着听吧。”
“好好好!只要吴先生肯说,我们跪着听也行。”
看官赶紧寻个好地方坐下,每个人都自觉地闭上了嘴,不发出一点声响,打扰吴先生。
吴先生从袖子里掏出扇子,扇出几阵风后,说:“这阿箩姑娘啊,吃了七爷的血后,啧啧,胖了不少……”
“什么!魂魄也会胖吗?”吴先生才说一句,就有人接嘴了。
“哈哈哈,自然。”吴先生回。
谢必安将阿箩残破的魂魄,一缕一缕地收集在手心里。
此时的魂魄损了根,受了惊吓,没有了任何的记忆。
阿箩做人做鬼时都调皮,不是个乖性子,谢必安在收集魂魄的时候,怕魂魄乱跑,他拔下自己的头发丝,将每一缕魂魄都绑起来,再十缕魂魄为一团打成一团,拎在手中。
但说来奇怪,今回阿箩的魂魄非常乖。
魂魄轻飘飘的,不经风吹,一吹则会跟着风儿远去,每回风吹来,阿箩的魂魄会抱成一团,主动紧绕在谢必安的大拇指上。
“阿箩……”谢必安声音轻虚清脆,叫了一声阿箩。魂魄似乎能听见,发出一些屑屑索索的声响来回应。
“你听得见吗?”谢必安用另一只手,去触碰大拇指上的魂魄。
魂魄和清晨时山林间的雾气一样,冰凉无形状,谢必安来触碰的时候,它们长了眼睛似,灵活地左闪右躲,避开谢必安的触碰。
谢必安收回了手,他不知魂魄左闪右躲的,是在怕他还是在闹着玩。
谢必安把阿箩所有的魂魄都收集起来,回到地府,寻了个拳头一般大小的药瓶养了起来。
侵晨的血液最新鲜,于是一到侵晨时分,他会割破其中一根手指,给魂魄喂血。
魂魄不知那是血,只觉得这东西味道香甜,饮之生精神气,便将谢必安的血当成浆水甜露来饮。
每日侵晨,魂魄就在药瓶儿里叫唤,叫唤着要饮血,有时候谢必安去阳间勾魂,未匝时归来,魂魄会大哭大闹,声音洪亮如钟,整个地府的鬼差都能听见。
吵得阎王爷都在哪儿发脾气:“阿箩这个小鬼,不管成什么样子都爱吵闹。”
实在吵得厉害,后来谢必安便将那药瓶随身携带。
但谢必安没有想到魂魄会长大变胖。
起初用药瓶装阿箩的魂魄还绰绰有余,魂魄在瓶里头能自由飘动。可百日以后,瓶内几无隙地,有的魂魄被挤扁了,贴在瓶壁里一动不动,看着可怜。
谢必安只好将药瓶换成了一个大葫芦瓶。
但也是在百日后,大葫芦也装不住了魂魄了,稍不注意,魂魄就会撞开顶上的盖子跑出来。
“还能长啊……”谢必安只好撇了大葫芦,请酆都城针线铺的鬼差,用软布金线,缝制一个荷包。
荷包有枕头那样大,谢必安想阿箩再怎么长大,也不该大到连荷包都装不住。
然而这回不到五十日,魂魄在一夜之间就大了三倍不止,谢必安醒来后看见荷包鼓鼓,还以为阿箩在里头玩闹,松了打口来看,魂魄一缕一缕的,如同水流倾斜,哗啦一下流了出来。
谢必安捧起摔在地上的魂魄,在手中掂了掂。
谢必安发现魂魄不仅变大了,还重了不少:“嘶……奇怪……这次是变胖了?”
没有人能回答谢必安的问话。
渐渐的,阿箩的魂魄长得和人一样大。
那些魂魄颇爱自由,每一捋都不愿被挤压,也就无法再装到瓶里或者袋子里,别无他法,谢必安只好让阿箩的魂魄生活在寝室里。
魂魄变大以后,需饮的血也倍增,养在药瓶里时,只需一两滴血就能喂饱,养在大葫芦里,也不过七八滴,到了荷包里,逐渐要用杯子来呈血液。如今养在寝室里,得饮满满一大碗的血液。
阿箩喜欢用金碗来饮血液,不用金碗来装,她便不肯饮,吊到横梁上呜呜乱叫来发气。
怪讲究!
有时候谢必安嫌放血太慢,割破手腕后就呼阿箩来,嘴对着破口处吸。
阿箩不贪饮血液,饮饱了就趴在谢必安膝上一枕黑甜。
魂魄没有五官,也无人之形状,但谢必安在这团魂魄里总能看到一丝阿箩的面貌。
一想阿箩用桃木簪子刺进自己的胸口中,好不容易投胎成人,又因他早早死去,谢必安后悔、自责,心也疼,他抚上一缕魂魄,颤声说:“阿箩,是七爷对不住你。你要快些好起来。”
阿箩睡熟了,并没有给谢必安一点回应。
每日要给阿箩饮大量的血,谢必安日日都是失血过多的状态,脸色白得发青,就连手腕上的青筋都变成了紫红色。范无咎见状,担心谢必安会因失血过多而倒下,便道:“这几日先用我的血来喂吧,反正二狗子饮的血不多,你歇息几日。”
二狗子和阿箩的情头一样,不过二狗子的魂魄破损得没有阿箩的深,且二狗子是糙养大的,除了饮血,还可以饮些酒水饱腹。
谢必安婉拒,虚弱地笑了笑:“阿箩现在还怕生呢,也饮惯了我的血,突然换成你的血,她会不高兴。”
范无咎用血喂了二狗子好几年,再过一段时日,就能做回从前的二狗子了。要想阿箩变成以前的阿箩,照这样的情头来看,真是盼不到一个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