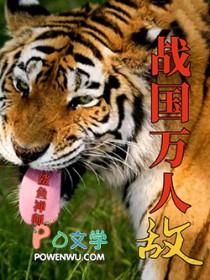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刘春山和秦灿 > 第1章(第1页)
第1章(第1页)
九十年代初,高中毕业的刘春河,在农村老家荒废了几年。
他满打满算的,上了约有八个月的班。
在县城一家数得上号的饭庄做传菜员,工作简单。
简单到只需要一天的入职培训。所谓的培训,无非就是强调几个动作要领,连岗位规章都算不上:站姿如何挺拔,托盘行进如何稳健而挺拔,传菜给桌前服务员如何顺畅而挺拔,之后退步转身如何迅速而挺拔。
敬请牢记俩字儿,挺拔!
“我天生挺拔。”刘春河不屑。
他而且天生自信,凭着这个天性,对这个岗位有一点儿挥之不去的鄙视。
“不然啥关系也不灵!这条儿长那了,天生臭美的,明天上岗!”
“是!长官!”
他有了工作。
挺拔几个月下来,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凭着他的年轻生猛,累就更是谈不上。
但是,令刘春河不爽的,出场费可怜兮兮也就罢了,整个班儿下来,连半句台词都没有,这让一向伶俐快嘴的刘春河有些按耐不住。
这一天天的!拿模拿样的装聋作哑。
“学学你爸。”母亲这样说他。
天生臭美的刘春河,却是从心底喜欢自己这身酱红色的工装。
他喜欢在人前耍那种,挺拔类的帅气。更是喜欢侧耳悉心捕捉,哪位客人偶然送给他的一句夸赞:哦,好帅!这会让他闭嘴一整天都觉得值。
以至于私底下他权衡了一下,不妨先喜欢着自己的哑巴岗位,从长计议。他甚至官宣,今后可以考虑主动兼职拉客。
主管说,人家那叫公关或者销售!你这一拉,进风月场了。
总之,有提成。
“来吧!一人也是客,仨也不嫌少!说我!可送大果盘!”刘春河放下电话,肚子里还留了一句,说我,咱有奖钱。
转天的晚上,预留了位置很好的一处散台,静候着初为掮客的刘春河促成的第一批客人。
六点半,大头携两位被他称作的狐朋狗友,如约而至。
一桌三人,三凉三热,两份水饺一荤一素,不喝啤的,就认五十二度本地清香型,两瓶。
“冷热菜水饺一起上!春河,忙你的去,别影响我们交流!”大头开着玩笑。
葱烧海参。刘春河的第一批客人,还是有道硬菜的。在短短而曲折的传菜路径上,他默默盘算着这一桌下来,大头的花销……
餐厅不小,容得下大大小小二十来张圆桌。
雪白的墙面上,贴着若干幅应时的宣传画,一米五高豆绿色的墙裙上端,则是窄窄的横幅标语。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冷冰冰的告诫和提示,防醉的,防火的,防盗的,防吐痰的,防打架的,防家庭不和睦的。概括一下,都是要求你及家庭及社会,务必保持干净卫生,安全无误,精神文明。
吃顿饭,人家要求饭前洗手,这儿要接受一次洗礼。
大头的头上,就顶着一条“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戒律。
那个年头,哪里有那么严格的清规,就更不会有那么主动的自律。所以墙上贴的宣传标语,除了应付管理部门去应付管理规章的要求之外,就是给孩子用的餐前识字贴而已。
何况三个人大言不惭自驾来的三辆自行车,说算不算的,啥律都没了。
没有后顾之忧的酒场,无论规模,均为战场,参战者,均是勇士。
约莫两个钟头的厮杀,三位勇士的状态,就是一个大头需要两个狐朋狗友的托架,方可勉强地挪到自己的车位。
那位被托架出来的大头,辱没了勇士的尊严。他绵软地瘫扶在后车架上,“呜哇呜哇”的引导着自己,像是在说,这肚子里的难言之苦,完全可以一吐了之。
大头的周身上下,任凭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几番地毯式的翻腾,也摸索不出来,那把被断定为单蹦个儿的自行车钥匙。
“我记得…是不是…给你了是吧。”大头把重音落在了“给你”上面,算是钥匙有了着落。
他的眼神呈发散状态,却不知道“你”指的哪一位。
“说啥?!”他的无赖遭到了回怼,屁股上还招来一脚。
“那就是,谁,那谁借走的!你说…我不借麽?!同学一场!我是…那种人麽?!”大头若有其事似的越发认真起来,话却说得越发糊涂。
“得了!开了也骑不了。”刘春河返身跑回后院,很快推来一辆厨房用的小斗车。
三人不知其用意,歪歪扭扭,站在他挺拔的身板下,成了略显猥琐的背景板。
“你俩负责送货到家!好在不远。”刘春河麻利地解下二人的钢丝锁,分别套在了各自后车架的两个侧端,
另一头,套在小斗车推把的两端,锁住,将同样是单蹦个的两枚钥匙,分别塞入两人的裤兜。
然后,舒不舒服的,三下并作两下,将大头折叠起来,扔进车斗。操作手法有些粗暴,惹得当事人发出来“呜嗷呜嗷”的声响。
“别吐斗子里!自行车我下班送回去。”刘春河随口嘱咐,并不指望他听得见。
唉!这涡卷在车斗里的一堆肉,实在匹配不上他那个儒雅的官名。黎立晓,倒是不如小号叫起来省舌头而且生动。
“你尽管用,用…就是。”大头,是个热心肠。
小说《房奴》第1章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