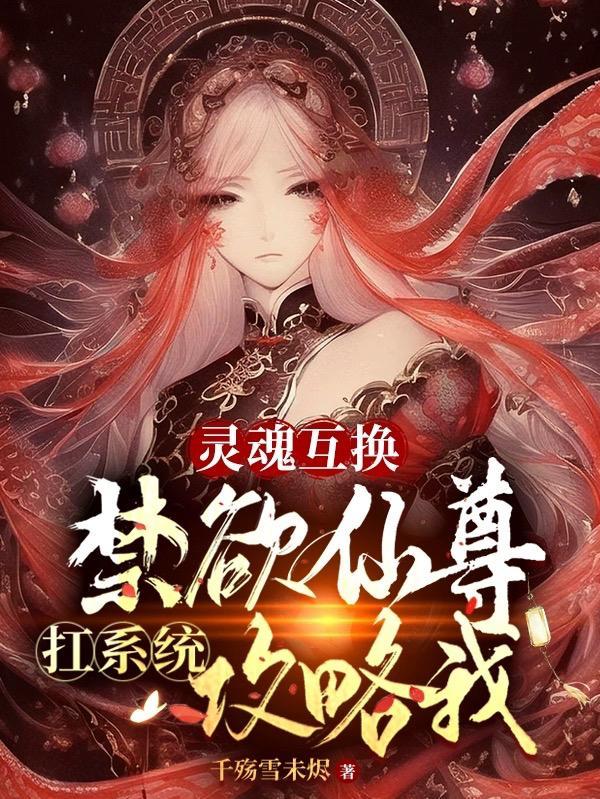布丁阅读>愚蠢假少爷活该被报复 无忧道人 > 第131章(第1页)
第131章(第1页)
他回过头来,拍干净司煊身上的积雪,又在司煊眉心烙下一吻。
“等着我…”
他朝着虔诚的跪拜下去,额头触地的瞬间,能听到积雪被微微压实的声音。他缓缓起身,再往上迈出一步,又一次跪下,周而复始。
寒风呼啸着掠过雪山,如怒号的野兽,无情地吹打在伽聿的身上。他身着当地人的黑袍,孤独的身影带着决然,一步一叩,一往无前的朝顶上行进。
叶昊拦住他:“二少,我以为你也是无神论者…别拜了!就算到山顶,死人也不会复生,还是还是早早入土为安才是…”
伽聿仍旧沉默的向上叩去,紧抿双唇,虔诚至极。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他的两只手便冻僵了,几乎失去知觉,但他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停顿。那冻僵的手依然坚定地触地、撑起,仿佛是被一种超越□□的力量所驱使。
两小时,三小时…
他仍然姿势标准,继续叩拜。而一旁的叶昊,不再言语,只是沉默的、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身后。
很快,夜幕降临,风更凛冽,如冰冷的利刃,无情地切割着一切。风卷着冰碴和雪花,无情地扑打在脸上,如刀割般疼痛。那刺骨的寒冷,似乎能穿透厚厚的衣物,直逼人的骨髓。
可伽聿依然坚定不移,朝山上跪拜而去。
晨光熹微,光线逐渐变亮,叶昊瞧见眼前白雪上出现点点殷红,他脚步稍顿,回头望去,只见身后皑皑白雪,一串鲜红血迹,格外刺眼…
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捂着眼跪倒在原地,嚎啕大哭起来,哽咽道:“二少啊,你别跪了,死了就是死了…人死不能复活!煊哥如果在世,看到你这样,他得多难受…”
整整三天三夜,上千米高,三万八千步,伽聿从雪山山脚跪拜到山顶,他的身后,鲜血开路…
这个矜贵了大半辈子的少爷,在蚌壳里娇养数年的明珠,磕磕碰碰都有一群医生围着,一直被无数宠爱长大的二少,从未如此惨烈过,即使他跌落神坛,也未曾被真正伤害过,知道现在,他额头已经烂成一块青黑碎肉,双手血肉模糊,早已失去知觉…
他跪在山顶上,沐浴在金光中,身前是模糊不清的石像,勾勒出人形线条,却没有丝毫雕刻痕迹,仿佛天然出现的,和雪山连为一体。
“鬼神,请让司煊苏醒。”他虔诚的一拜。
然而空中只有风呼啸的声音。
“鬼神,请让沈煊苏醒。”他又虔诚的一拜。
“没用的二少,快和我下山去医院吧!再晚点你真的要废在这了!”叶昊又气又心疼,沈伽聿为什么这么固执,为什么非要做这些无用功!!
“鬼神,请让司煊苏醒。”伽聿完全不受影响。
“孩子,即使代替他,后半生都要祀奉在我身前,你也愿意?”耳边突兀响起空灵浑厚的女声。
“我愿意。”伽聿虔诚一拜。
“你们两人真是胡闹,一个愿意以身为阵,给你强续生机,让你此生自由。一个又跪拜三天三夜,用后半生自由来换取对方苏醒。罢了罢了,赶紧走吧,一切只是回归原点而已…”
“谢谢鬼神。”伽聿敬拜后,转头对叶昊说道:“我希望你对司煊隐瞒我的存在,他已经失忆了,全然忘记我的存在。”接着,他强行站起,单薄的身体立于雪山之巅,身后白雪纷飞,他扫了眼身前的几个寨民,寒风呼啸中他的声线虚弱又泠冽清晰:
“从此刻起,我是新的阿父…”
黑袍寨民随之恭敬行跪拜礼,嘴里念着古语。
叶昊似乎还未从震惊只清醒,“二少…你说什么…煊哥他失忆…你为何要隐瞒他你们明明彼此相”
“曾经,他替我承担二十六年的责任,现在,我还他下半生自由…”
伽聿望着那漫无边际的白雪,呢喃着:“南疆,这次换我来守!”
命运的齿轮早早开始转动…
宿命,相互纠缠,却又无法彻底走进对方世界,吸引与排斥同频共舞…
这就是命运的绝响!
伽聿躺在寨民的担架上,被送了下来。
来到山脚,他走下担架,一个趔趄往下倒去,忽然,一双冰冷的手抱住他。
“喂你…你没事吧…”
眼前人身上堆满积雪,墨黑的眸子露出些许关切,扶着伽聿,没有半分逾矩。
这陌生的眼神,令伽聿心一痛,不知为何,泪水夺眶而出。
司煊呼吸一滞,且见此美人,眼下乌青如墨晕染,尽显憔悴疲态。额头之上,伤口处血肉模糊,狰狞可怖,肌肤苍白,毫无半点生气,宛如被寒霜冻结千年的冰雕,脆弱得仿佛轻轻一碰便会支离破碎。
雪白的发丝凌乱地散落,与血迹交织在一起,就像曾经的风华绝代此刻已被残酷的命运践踏得支离破碎一般。美人微微颤抖着,每一次呼吸都似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痛苦与无助在那黯淡的眼眸中闪烁,令人望之而心生悲悯。
心脏猛的一缩,司煊伸出手,想抚摸那双绝望哀伤的丹凤眼,下一刻,美人就阂上双眼,似乎沉沉睡去。
离那蝶翼般的长睫还有三厘米,只见一双冷感白皙、骨节分明的手,轻轻将美人接入怀中。
男人五官冷峻,眉眼之间蓄无尽暗色,恰似原野荒月,身着考究、挺阔有型的黑色呢大衣。其徐徐走来,每一步皆沉稳自持,身后之人撑黑伞为其挡雪。雪花浅浅,四散而开,连飘落之速亦似变慢。
他身姿挺拔,如孤松傲立雪中,散发着冷峻而强大的气场。那黑伞之下,仿若隔绝尘世,唯留他与怀中美人,似一幅绝美画卷,令人心醉神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