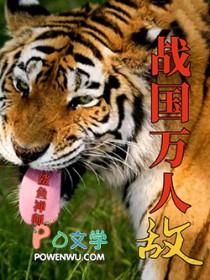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今朝春来打一动物 > 第109章 都在查蛊的线索(第1页)
第109章 都在查蛊的线索(第1页)
程雪松写了一张药方交给程心,“这个药你亲自做。”
施映雪从进门开始就一直紧紧地粘着阮玉薇。
施映雪有些恹恹地靠在她的身边,现在在偌大的京城中,她最为熟悉的竟然是她丝毫不知底细的阮玉薇。
昌宁伯府的境况与她所想,完全不同。
钟冠霖的院子不算热闹,但她总感觉有无数的眼睛盯着这个院子。
府里的下人也没有施府里的那些老油子看菜下碟,每个人看到她明明都是毕恭毕敬,可她觉得背后视线不断。
若不是今早钟冠霖病了,秋水火急火燎请了程雪松,她现在也没法出府拿药。
阮玉薇看着一屋子的人,她一肚子的话,只能硬生生地憋着。
她的视线突然落在程雪松的腰间,那个小竹筒。
是那晚,程雪松从苗岩的身上引出的蛊虫,就是在这个小竹筒里,她亲眼看着那条虫从黑色变成了白色。
她突然想到,她第一次见程雪松的时候,程雪松看着她时说的那一番奇怪的话。
无名和程雪松是双生子,她不知道无名是从何处习得前朝的禁术。
但程雪松的医术与其爷爷程太医相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是个醉心医术的人,得了这么一条奇特的虫,他必定会潜心研究。
程雪松在未触及蛊虫的时候,都能看出不同,现在是不是有了些不一样的认识呢。
思及此,阮玉薇有些犹豫。
她不信任无名,不相信他说的胡话,但是又不能全然不信。
现在她还没有万全的把握,不能冒险一试。
施映雪坐直了身子,回头看了一眼溶月,“秋水说要买那个什么记的糕点,你去买点儿。”
“是。”溶月退了出去买糕点。
施映雪看到溶月出了门,她才看向程雪松,“现在可以说了吧,钟冠霖的病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
程雪松看了眼还在场阮玉薇。
施映雪,“不用看她,她早就知道了,我第一回知道就跟她说了。”
阮玉薇默默抬手捂住耳朵,“我可以不知道!”
施映雪瞥了她一眼,“你知道的还少吗。”
阮玉薇,“……”
程雪松,“是真的,甚至是在他出去吴州前,都是真傻。”
“我寻到法子唤回了他的清醒,但是也仅仅是唤回,只要病就回打回原形。”
“这事儿,还只有我们几人知晓。”
说着他摸下了腰间的小竹筒,“现在这个法子的作用也越来越短,我却束手无策!”
施映雪也皱紧了眉头,“所以你的法子失效的那日,钟冠霖又会变成以前的模样?”
程雪松点了点头,“我已经翻了大量的典籍,偶然间在前朝的禁书上看了点儿线索。”
“但是前朝的禁书都是巫蛊之术,真正有用的不多。”
“苗栗族分医蛊两支,但是现在苗栗族的人仅存百人,这些人当中多少精通医理的又不得而知。”
阮玉薇若有所思道,“钟大公子是中了蛊吗?”
程雪松有些讶异地看了一眼阮玉薇,他又想到,给钟冠霖治病的这条虫,是阮玉薇送来的那人身上所得。
他点了点头,“也算是,按照现存的书籍,他应该中的是蛊毒,不是蛊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