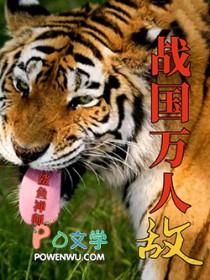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打工三十年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林羽翼的床位很幸运地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没在走廊。王登高停在房间外,透过玻璃往里面望,他的目光掠过前两张床上的病人,掠过蜷缩在一旁休息的家属,掠过角落里堆放的杂物,最终落在最里面那张床上。
林羽翼躺在那里。
她安安静静地躺着,闭着眼,脸色异常的苍白虚弱,可是脸颊上又泛着滚烫红晕,看起来极不正常。她那头杂乱如鸟窝一般的短发这时无力地耷拉着,碎发快要遮住紧闭的眼睛,发丝随着她呼吸的节奏轻轻颤,一点儿没平时那股活泼的野劲儿,反而衬得她异常乖巧可怜。
她旁边吊着一瓶透明液体,药液沿着滴管一滴一滴往下落,滴进她手背的针头里。
王登高看见她手背好几处红点,红得发肿——妹妹从小长得瘦,每次去医院打针抽血,护士找血管都要找好一会儿,想必这回也刺了好几针。
一想到妹妹平时打针抽血时,明明怕得要命却还要强装镇定,一滴眼泪都不肯流的样子,王登高只觉得心痛得要命。
他安静站在病房门口,眼眶无声地红了,不是像之前那样血管布满眼白时发疯似的红,而是心痛时的红。
王登高抬手抹抹眼泪,在房间最角落的位置,看到挨着墙闭目休息的王大元。王大元脸色同样很虚,就算闭着眼,他额头上都露出一条条疲惫的纹路。王大元瘸了一只腿,身体又一直很虚弱,他一个人把生着病的女儿从新村拉扯到广都来,可想有多累。
这时王大元正好睁开眼,目光好巧不巧和门外的王登高对上,他艰难杵着拐杖要起身,王登高急忙摆摆手让他别动,自己推门走进病房。
“爸,你辛苦了。”王登高看看躺在床上的妹妹,扶住王大元,压低声音,“小鸟她怎么样?”
“不知道。”王大元叹口气,“检测报告在那边,就是查血的那几项,在镇上就已经查过好几次了,我也看不懂。”
王登高捡起报告看几眼,密密麻麻的英文指标和数字,看得他眉头越皱越紧:“我去问医生。”
“我问了,医生说她可能烧成肺炎了,先打个点滴看看情况,之后量个体温再看怎么办。”王大元埋头揉揉额头。
“爸,她病多久了?”
“前天开始的,她一发烧我就带她去乡上看了,结果看两天烧还没降下来,乡上医生让我把她带广都来。”王大元说话时一直低着头,语气很是平淡,但他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王登高。
王登高一眼就看出,事情远比王大元口中说的那般惊心动魄。
不然……村里人也不会那么急切地打电话到他工地上。
王登高低头,看见父亲裤脚和鞋子上沾着的泥土,不仅是裤脚,膝盖上都剐蹭上了泥渍,他的手掌手侧,有很明显刮擦的痕迹。王登高几乎能想象出来,发现妹妹发烧的那一刻,父亲是有多慌乱焦急地起身,一手杵拐杖一手去扶她,结果自己一个没站稳,摔得差点起不来的样子。
王登高觉得鼻尖更酸了:“爸,小鸟她生病,你怎么不和我说呢?”
“和你说有什么用?”王大元语气倏地尖锐,这半年来,每每谈起儿子不读书的事儿,他总觉得心里堵,他当初是答应了,可他还是不舒服,每次王登高回家,他们都得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不过这回,话一出口,王大元自己都怔一下,他叹口气,声音明显降低了:“我只是觉得,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怕打扰你,你上回不是说,工地上忙得紧吗?”
“工地……”王登高张口差点把工地停工的事儿说出口,他立马剎住车,转而道,“工地那边忙是忙,但是爸,你想想,正因为我长大了,我才有能力也有责任帮你多分担点儿,不是吗?我出去打工的时候就说过,我赚钱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你和妹妹,她都病得这么严重,你还不告诉我?怎么想的呢?”
王大元没说话,粗糙的手指搓了搓。
王登高心里默默地叹气,转身摸了摸妹妹的额头,他被烫得一下挪开有,眉头越皱越深:“这多少度?真没问题吗?”
他声音控制不住地有点大,陡然惊醒了已经睡着的林羽翼。她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眼眸里布满雾气,浓密的睫毛轻轻颤着,她无神的目光一点点找到焦点,看向王登高,虚弱地眨眨眼:
“哥哥……”
“小鸟,哥哥在这里,哥哥在。”那一刻,听着妹妹破碎虚弱的声音,王登高觉得自己心都要跟着碎掉了,他小心翼翼握住林羽翼的小手,“小鸟,你好好休息,会没事的……哥哥在这里,哥哥一直陪着你好不好?你、你饿不饿?想吃什么吗?哥哥去给你买……”
林羽翼没有回答王登高的问题,她看着她,唇角艰难地往上翘,露出一个无力的笑,笑容才显现一半,又因为没有力气耷拉下去,她闭上眼,又一次昏昏沉沉地睡去。
……
终于打完点滴,护士来给林羽翼量了次体温,随即她的眉头皱起,快步离开病房。很快医生过来,摸摸林羽翼的额头,看看化验单,然后凝重地对王登高二人说:
“我建议你们带她去蜀医看看,她发烧这么几天始终降不下来,很可能是肺上被感染了,但具体是什么感染,我们医院没那设备,查不出来,他们蜀医的特效药,我们这边也没有——我们能治是能治,但只能按照常规的方法来,至于多久能把烧降下来?这个我不能保证。我建议还是尽快带她去蜀医,去那边照个片,了解清楚病因,才能尽快地把烧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