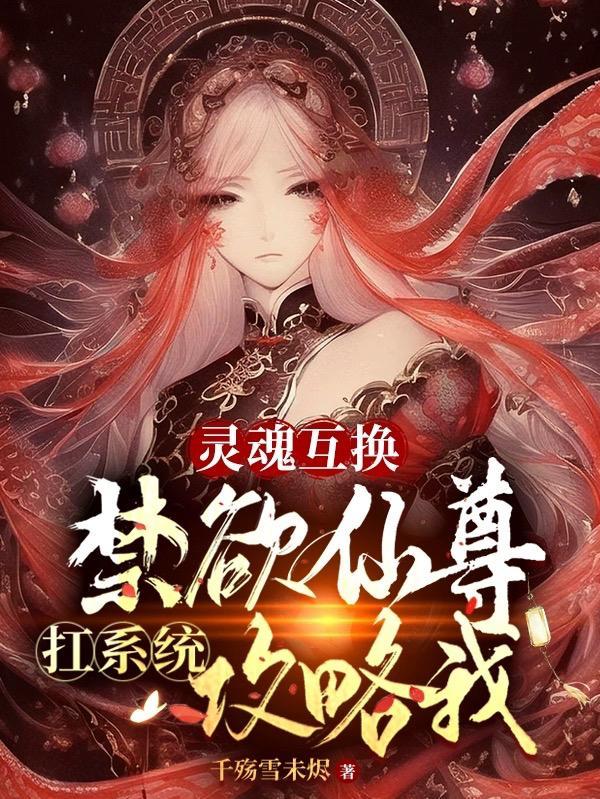布丁阅读>明月不谙离恨苦打三个数字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原以为入太学是很快的事情,但她没想到最后难搞的依旧是江诉,她每写一篇江诉就找出她的改进点,好像入太学近在眼前,又像遥遥无期。
她十分怀疑是江诉在整她!
江诉每每问起是否疼时,她嗷嗷几声疼,将所有不满的情绪都铺露在脸上和声音里。
有一天她十分认真地问江诉:“我明明已经将你所说的东西全部写完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去太学!你是不是故意的?报复我上一世……”
“没有。”江诉反驳道,“我既不恨也不怨,县主与其耗费时间与我争执,不如先写,这处还有问题。”
枕清瞧着硬的来不了,于是道:“江诉,我腰疼,头也疼。”
连日来,不停歇地翻阅书籍,就算是没腰疼,也要头疼了。
江诉妥协道:“我改,到时你再温习一遍。”
枕清得逞,当即一个转身看向窗外,净眼净心,可曲起食指敲打在窗格上的动作,难以掩饰她心中的焦躁不安。
时间不多了。
笃笃笃的敲打声落在了江诉的耳中,他看向浸在盛阳里的枕清。
她撑着手懒懒地托着下巴,眉眼虽是舒展,却也挡不住几许忧愁,紧致上翘的鼻子划出一个弧度,勾勒出几分安逸,紧抿的唇瓣紧绷着。她曲起食指敲打的动作毫无规律,像是错乱的思绪。
她在着急,很着急。
这么清风疏朗的天气也吹不走她的情绪。
江诉搁下笔,缓缓道:“县主在急什么,这不是还有我吗?”
闻言,枕清睁开眼,入目亮丽的景致在睁眼的那瞬间一片恍惚,就连她的心神也跟着晃荡,在看清安宁的风景后,心也跟着平稳下来。
她觉得可笑,有他又能怎么样,说得好似他能一直帮她,而她能对江诉毫无保留地倾诉似的。
可是江诉真的没有帮过她吗?
是有的。
只是她不敢信。
枕清耸了耸肩,脸上的神情并不正经,她笑嘻嘻地问道:“江中丞,你会帮我吗,一直一直帮我吗?”
江诉认真望着她,轻声道:“我会。”
枕清侧过脸,她有那么一刻恍惚,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一点点敲开,这样的敲动并非是蛮力被迫为之,更像是她自己自愿的。
她本想继续维持假惺惺地笑,可唇角忽然抬不起来,于是她不笑了,露出原本的样子。
“如果我做的事情不好呢,有可能误入歧途,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那样是对还是错,江中丞也会帮我,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帮我吗?”
就好比禹王,她杀了禹王,可是依旧有很多百姓爱戴禹王,觉得禹王是个顶顶好的人。
而她为了一个从来不记得的枕家杀了禹王,杀了一个养她那么多年的人,有错吗?
枕清轻轻一笑,忽地叹息,笃定道:“我想,你不会的。”
“世间万物的对错对于每个人而言,没有一个特别的绝对性,如果你真的做错了。”江诉也转过脸,望着她道:“那么,我会在你误入歧途前,拉住你。”
前日禹王的话犹如在耳畔。
禹王略有怅意道:“沿溪的性格执拗,太容易固执己见。来听,在将来的某一天,我需要你来拉住她。”
江诉声音低荡温和:“下官会的。”
这日后,江诉一如既往地问起她疼不疼,她说了句不疼,于是那天特别顺利,江诉果真放过了她,说可以入太学了。
后知后觉和江诉耗费了一月有余,回过神来想想,并非是江诉留着她不想让她去,而是想让她伤好了再去。
这一刻,枕清觉得自己像是被江诉用心浇灌的花,其中耗费许多精力,可是他并不说,待自己察觉后,那股情绪在胸腔中,如同崩流,顺势而下,势不可挡。
秋山海远杳千重(五)
太学很大,占地有百亩,分很多个院门,人数也众多,所有门生都有统一佛青色的服饰。枕清拿到衣服的时候,还看了好一会的衣服,走在前面的博士时不时回头瞧上一眼枕清,跟她提醒道:“太学离不管你的家世、样貌,大家同等对待、吃住一致。”
“好,门生记下了。”枕清嘴上应得好,心里却是一点也不信。
大启的学堂不止有太学,还有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别看都是学校,这里面也有极大的差别,入学也和学生祖父官爵有关。
例如太学和四门学,分别是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至于律学、书学、算学,则是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
和她说什么同等对待,要是家中没点权势,连太学的边都摸不着。
枕清看着自己手中的衣饰,又摸了摸材质,也算是上乘的布料,或许这太学的初心是好的,若是真有特别富足的富家子弟腰间挂满玉坠,又穿着名贵绸衣,也叫人不敢招惹和小瞧,或许连带着太学的风气也被带坏了一遭。
“在太学里的学生可享受供膳,但要向老师行‘束’之礼。”走在前方的博士停下,回过头看向枕清。
枕清见人停住,她抱着衣服也跟着停下,唇角微微带笑,示意博士继续说。
那博士问:“这个礼节你可知道?是学生与老师初次见面时敬奉的礼仪。太学里,需要送绢三匹,当然也会有酒肉,量力而行。”
枕清点点头,问道:“此目的是为何?”
博士解答道:“目的是密切师生关系。”
枕清听罢,微微一笑,去一个小房间换了一身衣服,找到一个空处的角落里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