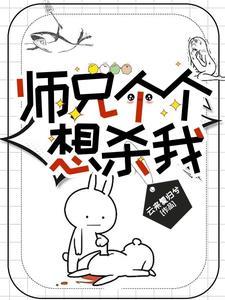布丁阅读>京城模范夫妻互穿后先婚后爱 > 第7节(第2页)
第7节(第2页)
然而他却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崔令宜并不是在为自己的东西被妹妹占去而郁闷,而是她突然想起来,那盆兰草的泥土里,以前被她偷偷倒过一些毒药化作的药水,为的就是测试会不会对植物产生影响,免得日后要用时,不慎留下破绽。
测试结果是不会,那她便没再管这事。
但现在花盆被六娘要走了,她既然喜欢兰草,又只有七岁,难保哪天摸了泥巴的手又去摸吃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崔令宜可不敢保证药效还在不在,一想到六娘哪天可能会突然暴毙,然后顺藤摸瓜查出有人在花盆里下毒,她就觉得眼前一黑。
不行,得赶紧想个办法解决才是。
第9章第9章
卫云章作为一个公认的好女婿,在崔家度过了和谐的一天。
到了夜里,夫妻分房而睡。卫云章躺在床上,手臂一伸,只摸到平坦坦空荡荡的床板。他望着床顶,忽然觉得有点寂寞。
明明之前也是一个人睡的,但只是与她同塌而眠了两夜,现在便觉得一个人的夜晚格外寡淡起来。
卫云章叹了口气,忍不住抓了下头发。
头有点痒,感觉恋爱脑要长出来了。
他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皎洁月光落了满怀。
古人对月思乡,他却在这里对月思妻。明明是住在同一间宅子里,他却不能去找她。
一阵秋风过,树影婆娑,惊动了鸟雀,从屋檐上低低闪过。
这个时候,她在干什么呢?想必是已经睡着了吧。卫云章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像个毛头小子一样,十分好笑。
月光如练,“已经睡着”的崔令宜,正一身黑衣,在京城的屋檐上穿梭疾行。这条路线她已经走过几百次,甚至对夜间巡逻的士兵布防都了如指掌,绝无出错的可能。
夜风贴面而过,她悄无声息地翻上酒楼的窗户。脚下是几丈远的地面,她一手攀着窗台,一手撑开窗户,像一只轻盈的野猫,又像一片倒流的乌水,倏地钻进了窗子里。
窗户又安静地合上了。夜色中,打烊的酒楼静静矗立,仿佛无事发生。
崔令宜穿过暗室,推开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个绛色衣袍的男人正坐在桌边,自斟自饮。见她来了,放下酒杯,淡淡道:“你总算是来了。我还以为你新婚燕尔,不能自拔呢。”
崔令宜哼笑一声,在他对面坐下:“卫家是什么地方,你都混不进去人手,还指望我一个人人瞩目的新娘能干什么?”
男人道:“若是干不了,就去跟楼主说一声,这任务你别接了。”
崔令宜:“你急什么?是怕事成之后,我把你取而代之?”
男人道:“我听人说,你今日回门,与卫三郎郎情妾意,好不恩爱。我是怕你昏了头,忘了自己要干什么。”
崔令宜嗤了一声:“我才嫁进去三天,要是这么容易就昏了头,那卫三郎就该是妖精变的了。”
“女人的心思可说不准。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女暗桩接近猎物,最后背叛拂衣楼的前车之鉴。”
“所以她们都死得很惨。”崔令宜笑吟吟道,“与此同时,死得很惨的还有自以为是的男杀手,被同伴的表象所欺骗,掉以轻心,最后却被反杀,成了他人竞争上位的跳板。纪门主,你说是不是呢?”
她拿起酒壶,给自己面前的空酒杯满上,刚送到嘴边,脸色就变了。
“你敢毒我?!”
瞬息之间,原本在她手里的酒杯,已经凌空而起,出现在了纪空明的颊侧。
冰冷的杯壁与他的肌肤一触即离,纪空明拍案而退,酒液尽数翻倒于他的衣袍之上,空杯则被他稳稳钳于指间。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刺痛,他看向手指,只见一枚银针紧紧贴着杯壁,半根已没入他的指腹。
他眉头一挑,松开手,把银针拔了出来。
几滴血沁出,被他随手抹去。
“看来你不曾退步,倒是我掉以轻心了。”纪空明说。
崔令宜哼道:“你该庆幸我与你不同,我可没有下毒。”
纪空明捋袖,重新给她倒了一杯酒:“说说看,在卫家都有什么收获?”
崔令宜饮了一口酒,道:“我最近会抽空把卫府的新地图画好。至于所谓的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地方,是一座荒废的庭院,我还没来得及进去。”
“那什么时候去?”
“白日里人多眼杂,夜里卫三郎又在,我还在等机会。”
“卫三郎一介书生,对付他,很难吗?”
“说得轻巧,你行你上。”
纪空明:“行,我不催你,你自己有数就好。对了,你来看看,这张纸上可是卫三郎的笔迹?”
他推来一张细窄的纸卷,崔令宜将它抻平,端详半晌,道:“确实是他的笔迹。这是什么?”
“你与他成婚前夜,我们的人,从卫宅外截获了一只信鸽。”纪空明转着酒杯,幽幽道,“这上面写的,其实是一首藏头诗,你看开头四个字,合并起来,就是‘明日故地’——你觉得,他要去见谁?”
崔令宜皱起眉来:“他能见谁?成婚当日,他不可能有单独行动的时间。”顿了一下,她眼神一凛,“不对,他那天夜里,并不在卫府。”
纪空明轻轻敲着桌子:“太皇太后崩逝,他进宫去了。但这也不能代表所谓故地就是在宫里,除非他能提前预知太皇太后的事。所以,我更倾向于你们成婚那天,他在卫府里悄悄见了什么人。你说,他一个当官的,有很多独自外出的机会,有什么事是需要这么着急见人的呢?”
崔令宜神色凝重:“我会想办法查出来。”
临走之时,她补充了一句:“国丧期间,规矩颇多,这一个月里,我都不会再出门了。”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