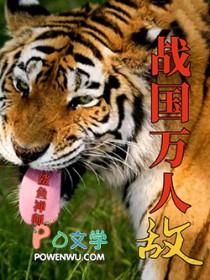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小美人怀了协议老公的崽免费 > 第20节(第1页)
第20节(第1页)
薄寒臣紧盯着迟诺纯稚的脸蛋,试图从上面寻出一丝蛛丝马迹,引诱着说:“正常人都会有需求,这是生理本能,不会随着嘴巴的否定就消失殆尽。”
迟诺根本不吃这一招,舔了舔唇:“不会,我绝育了。性盛致灾,割以永治。”
薄寒臣:“……”
两人这一争论,留给他们收拾东西的时间就不多了。迟诺给自己塞了两包小蛋糕,往里面按了按,不让薄寒臣看到。
本来是有薄寒臣一个的,现在没有了,薄寒臣不配吃他的小蛋糕。
薄寒臣不是瞎子,自然看到了他的动作,其实迟诺在朋友之间表现疏离的方式比较幼稚,很少真是与人撕破脸皮,偏偏他这幼稚的举动挺刺挠人的。薄寒臣心里泛起了一丝躁郁,抓住了迟诺的手腕,将两人的距离拉进。
那截手腕纤细雪白,细腻盈透好似轻易就能折断的玉簪。
薄寒臣松了点力气,“你在生我的气?”
迟诺从小到大都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遇到事情很少回避,一直都是更倾向交流解决。
除非无法交流。
迟诺纤长的睫毛轻颤,认真表达着自己的不喜欢:“有点。你刚才好凶,我有点怕。”
凶?
薄寒臣眸色轻柔了几分:“任何人看到那种东西都会往那处想。不是和我,就是和别人。这种思考逻辑没错吧?”
确实。
不用还放在背包里,骗傻子吗。
迟诺本来就心虚,噘噘嘴:“好吧,”顿了顿,说:“以后不许凶我了哦,像我这样好哄的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薄寒臣淡笑:“确实。能哄到你,是我三生有幸。”
迟诺雪白的脸蛋被他的话臊红了。
狗东西真的很会!顺坡!!下驴!!!
大概是薄寒臣的调笑声太过温文尔雅,原本如冰一般冷凝的气氛全散干净了,反而有一种很微妙的
暧昧感。
迟诺先在这种氛围中败下阵来,转身开门。
薄寒臣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忍不住描绘起来迟诺纤薄的肩膀和细瘦的腰肢。
两人已经换回常服,盛夏末梢的温度依旧很高,衣衫也比较薄透,雪白的衬衫,腰线紧收,细泠泠的一截腰,衬得他更似薄雾中盛放的玫瑰花的枝干,柔又韧。
衬衫下摆塞在西装裤里,臀部挺翘,显得那截腰更加勾人了。
只有薄寒臣自己知道,他是个十足的腰控腿控,世界上能在这两点上满足他的视觉感观的只有迟诺。
如果迟诺也控他的腰和腿就好了,这样比较公平。
薄寒臣小时候就目睹过夜场的交欢行为,在他眼中做愛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事情,他完全没办法认同,人类用极其下流的动作去亵弄爱人的行为。
他认为自己一生都可以不沾染情欲,直到某天,他梦见了迟诺在他身下哭,浓黑卷翘的眼尾挂着泪珠,虚弱地看着他,似娇似嗔。
他竟然会更比他见过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更加恶劣,更禽兽,更下流。
也许是真的憋久了。
才会对着那张清纯而伟大的脸,浴a火焚身。
可是当下他最想确定的是,他和迟诺是否真的做过。
如果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