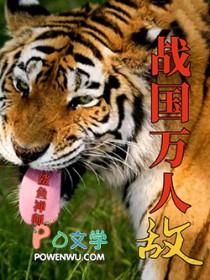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叹息桥演员表 > 第8章(第1页)
第8章(第1页)
小小的理发店里一片寂静,四下无人,李霜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凌晨三点半,红姐和她的姘头此刻正在出租屋酣睡,理发店是无人打扰的小天地。
李霜央着秦欢解开胸前的扣子,露出胸膛,两粒乳头沾了冷风,很快兀立起来,依旧很红。
李霜瞧着秦欢一片狼藉的胸口,还是动了贪嘴的馋心,将那对乳头含了又吻,放在口中吮吸,直将乳尖边的皮肤啃出一片嫩红。
秦欢倚在镜台边,也不阻止,放任李霜像一个渴奶的孩子般在他的胸前舔吻,他微微仰起头,享受着李霜的玩弄带来的电流般的快感,口中泄出几不可闻的叹息。
李霜一边吻着他,手里挖出一大坨油膏,搽在秦欢的乳尖,接着转圈抹开。秦欢喉咙里抖出吃痛的吸气声,但乳头被李霜的手指揉按着,疼痛中更有快感,细细密密,似针扎又似猫挠。他本想着自己已经再没有那心思,但痒意却深入骨髓,隔着皮囊难以抓挠,恨不得有一对唇齿能贴上了吮一吮,吸一吸,深入其中搅和乱了,才能止痒。
他身后的镜面层层折射,将他们交迭行淫的身影无尽映照,四下洞见,镜像相照,人间淫戏。
借着路边街灯,他们在昏暗的理发店里又干了一次。李霜将秦欢压在平日客人用来洗头的旧沙发躺椅上,胡乱扯了干发用的毛巾垫在身下,掌心里没有抹尽的油膏全用在秦欢的后穴上,顺利地完全插入。
这是他熟悉的环境,每日工作的理发店,向来是他者的李霜此刻将自己的欲望宣泄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有一个瞬间里他想起了红姐和他的小师父,那对借着他人熟睡在黑暗中颠鸾倒凤的男女此刻好像附身在他们身上,手把手教李霜体尝偷情的刺激。
李霜进得又缓又深,每一次深抵都激起秦欢克制不住的颤栗,他们压抑着自己的喘息和身下的撞击,生怕惊醒了周遭正在睡梦里的谁人。秦欢的面孔浸淫在昏黄黯淡的灯影里,像一只耽于享乐又片刻即逝的野魂,他的眼角一片湿润,惶惶间回头向李霜看来,竟显得楚楚可怜。
李霜被他看得心头一软,伸出手去,任秦欢咬住自己,同时下身大力挞伐,压抑的性爱将高潮碾压得细如雨泄,他终于听见秦欢呜呜的哭声,他的身体在李霜身下紧绷如弓,他将手探向秦欢的性器,不意外触摸到一片湿热。
他又把秦欢操尿了。
李霜知道自己闯祸,连忙将自己抽出来,抵在秦欢的腿根射了。他覆在秦欢的身上,不停地亲吻他细腻光洁的后颈,安慰似的唤他。秦欢哭得停不下来,湿热的饱经折磨的后穴不住痉挛着,紧贴着李霜的鸡巴喘息。湿软的软肉在这摩擦之间,蓦地发出了一声屁般的轻响。
还在哭泣的秦欢顿时哭不出来了,俩人傻楞了一会儿,秦欢伸手扳过李霜的脸,像是因为这控制不住的屁响最后恼羞成笑,泄愤似地一口将他咬住。
“你这个饿狼崽子!”
李霜任他咬着,轻哄似的揉着秦欢白面团般的屁股,他没见过秦欢如此急赤白脸,刻下见了,只想得寸进尺。
“我错了。”他用仅存的自由嘴唇亲了他一口。
“下次还敢。”
【作者有话要说】
假期结束辽~下周开始周更
糖也撒的差不多了(。
纸盒
在理发店的隔板间里蜗居了三个月后,李霜终于有了新的落脚。
房子是从红姐的表亲手里借下的,房子几乎难以称作是房子,七面半的墙,门朝大街开,实则是老民房前沿的保安室。如今人去楼空,保安室如破纸盒一般矗立在一落粉身碎骨的危楼边缘,霉苔遍布,年久失修,命运岌岌可危,守护着人去楼空的凄凉。
除了囊中羞涩的外地打工仔,这样破败的房子不会受到市场任何青睐。
附近的人都说那是棺材房,房东深陷于迁地赔款的合同中,是与政府与时代争利益抢粥吃的投机分子。
红姐与房东是表亲,狭长的细眼宽阔的鼻翼,作为女人的面孔,在一定的年纪内尚能显得娇憨,但作为眉目相似的男人,这样的面孔更添奸诈。李霜说不上姐弟两人谁更精明,谁更会算计。
李霜签字的时候,房东痛快地将桌上五元一瓶的廉价白酒豪迈吹底,直说李霜是他的恩人;接着他感时怀伤地讲起自己在老房子里度过的童年,穿着开裆裤的岁月,并在怀旧的叙述里,用筷子夹走了盘子里最大的一块红烧肉。
李霜笑得稀碎,搜刮着肚子里不多的奉承言语,直说他和红姐才是自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最大的恩人。
酒过三巡,房东挤弄着精光细眼,鼻息耸动,凑近李霜耳朵边,告诉他,除了偶尔有拆迁办的人上门骚扰,住在此处的他不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房子只有一居室的大小,外沿接一个两人宽的天井供洗漱,如厕则需要去五十米外的公共厕所,房子离大街只有薄薄的一层水泥墙。逢雨季时,较高的街面上的雨水便会汩汩淌进地势较低的房院里,李霜在入住的第一晚就体会到了雨流成河的滋味,他忘记了门口放着用来赶水的沙袋,只能站在老木床上,用脸盆将流进来的雨水一盆一盆地舀出去。
除此之外,李霜的入住经历还算愉快,他一个月只消花费两百元,就可以免去寄人篱下抑或幕天席地带来的困窘。他的睡梦里不必再聆听男女情事,有的只是纯然的寂静——属于废墟的,荒野的寂静,偶尔有野猫野狗翻动瓦砾,引起的小小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