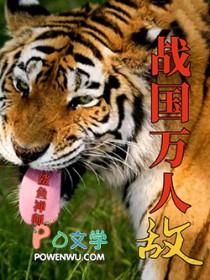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不仅仅是喜欢薄荷还有什么 > 第22章(第1页)
第22章(第1页)
……
救护车的声音变得瘆人。
接近六点的雨天提前迎来了黑夜。
宋楠的手里使劲攥着一份心理诊疗记录,上面的墨水寥寥,但字迹于许珩而言绝不陌生。
他尝试过只当宋楠是病人,可这份努力与尝试告罄。
他失败了。
薄薄的纸张上透着几颗晕开已风干的水痕,左上角有折叠的折痕,是许珩习惯性用指腹的摩挲,而记录上的日期是半年多以前,是许珩最后一次提笔,然后在上一次停顿的地方接着写下的新的诊断。
——拟改变消极的行为习惯以及思维模式,效果待考量。
可最后一个字落在纸页上还余水墨的光,又被他重新划掉了,旁边潦草的一团重重的黑墨圈,不知道笔尖在上面留了有多久,才会如此狰狞。
这是许珩给宋楠进行的最后一次无意识心理疏导,也是最后一次诊断。
他记忆犹新。
因为那是他彻底放纵自己去爱自己的病人的开始。
学心理的人心思更重,他们掌握太多理论和技巧,所以得心应手地将心理世界埋得更深。
尽管那不是许珩的主业,可他毕竟是真的拿过执照。
心理医生爱上病人,本就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不幸。
而宋楠太过敏感,也太容易揽责。
他不希望许珩无时无刻担忧自己,也接受不了自己不能给许珩提供必要的情绪价值。
那样,他会累,许珩也是。
宋楠总是反驳自己是个善良的人。
但不善良的宋楠会为了许珩收敛锋芒,会为了另一个人宁愿折断翅膀。
哪怕他不快乐。
许珩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宋楠不是不喜欢,而是他们其实都不太会应付喜欢。
莽撞的求爱者,最终撞得头破血流。
陈文问他:“你知道他在逼着自己顺从你吗?”
砰的一声,许珩只觉得心脏的位置被重力撞击,钻心的痛细密涌来,眼前的画面像是在旋转,他脑子嗡嗡作响,直到后背靠在墙上,他才低头看到自己颤抖的双手。
陈文为难地观察着他的表情,沉静地叹息。
“虽然说这样的话显得我的专业水平不到位。”他也很无奈,“但是,许律师,他始终都在抗拒我,用一个让我极度自愧的表达来形容的话,他接受我的疏导或许只是因为,不想再吓到你。”
这个叫宋楠的病人是陈文职业生涯里最大的挑战。
他唯一主动与他袒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陈医生,我不想再吓到他了。”
“你我学的同样的内容,应该清楚原因。”陈文的声音经过听筒,被电流声压得断断续续,“许珩,宋楠在愧疚,但是很遗憾,我不知道他愧疚的真正原因。”
啪嗒。
最后一根线禁不住紧绷,彻底断开了。
他第一次感到无力,甚至无比后悔。
他将宋楠当做一根浮木,所以曾暗自责怪他迟迟不肯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