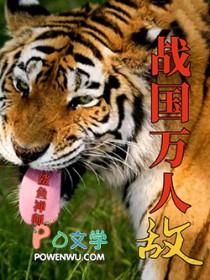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深海水母有哪些 > 第15章(第2页)
第15章(第2页)
上了四年级的我开始寄宿,因为我爸妈忙碌地穷着,没有时间管我。
那时候我的爸妈问我会不会想家,我从小就是个诚实的孩子,我不会,我从不想家。在学校我成绩不错,可以得到老师的关爱。即便半个月回去一次。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我跟别人稍微有点不一样,到初中高中大学,在外边住了十几年,毫不留恋故土。
所以我也有机会去修正自己的性格,不去斤斤计较,不去拜高踩低,不去嫉妒别人。但我始终不曾学会毫无保留地去爱。改了很多年,后来考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辅修了很多课程,打开自己的见识,去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
当然是痛苦的,但是都已经过去了。
人不能反复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这没有意义。
在大学阶段完成精神上的独立之后,毕了业就找了机会毅然决然去了国外。
然后打工,创业。
我经历过的感情里,从来不会在乎沉没成本,一个经济学概念,有时候会觉得经济学理论更容易彰显人性给人启发。
经济学的假定是所有人都是理性人,即有益处进入市场,无益处退出市场。所以当一件事情注定破碎的时候,不论前期投入了多少精力金钱,都与现在无关,沉没成本不影响当下决策。
而我的前对象们,都是被我看到了注定的未来之后断崖分手的。
但是似乎也是太过于理性而没有半点人的味道,而我自己,也在受此折磨。
……
一场无意间促成的聚会。
到了后半场的时候万山雪也来了。
万山雪上下西装,和这股精英范形成反差的是她的狼尾卷发,皮鞋换了另外一款琴底鞋,敲在地面上的声音让人沉醉。
她被引到三楼后,佣人就离去了。
现场几个男人的表情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只是我没在意。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圈,走进来绕过舞池随手脱了外套,扔在了沙发背上,酒红色西装马甲随着她的动作起伏,在吧台后站定,威士忌加了少半杯,金桔汁、柳橙汁、红石榴糖浆也加了不少,她调了两杯第八区。
随后在震天的音乐中走到沙发前递到我面前,坐到我旁边。
凑近我耳边说,有酒的话就必须得有故事。
故事是第八区的由来。
“这酒名字来源于上个世纪的波士顿民主党政治大头,artloasney,他老哥当时说过一句话:neverwriteifyoucanspeak;neverspeakifyoucannod;nevernodifyoucank是贪腐的代名词了已经,而这杯酒就是为了庆祝他的当选,第八区是他的选区,当时调出这酒的tohsion是他手下的人、locke-obercafé是他名下的店。”
“算是一个下酒菜。”她又淡淡说了一句。
“所以现在咱们也庆祝点什么,……为我们庆祝吧,世界上太多人了,有缘的没几个,可是我们很有缘。我以前拉过一个表格,关于人一生中会遇到的精神契合的人,排除掉地域因素,便不剩多少了,所以遇到一个就要格外珍惜。”
她微微低头,眼神盯着我,似乎出了神。
杯子碰撞的声音在无处不在的音乐中显得格外清晰,随后周遭的嘈杂开始恢复。像是上帝为这一刻清场了一般。
我靠在她的肩上,“那片灯光好像水母。”指着墙壁上游走的灯光。
“什么?”
“水母。”我靠近了她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