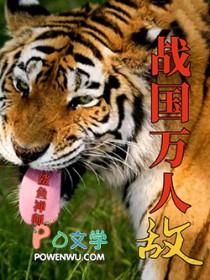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师尊我觉得 > 第108章(第1页)
第108章(第1页)
贺峋看着徒弟脸上浮现出的些许困惑,感觉人应该是误解了什么。不过这并不是能够被立即纠正的事情。
于是他只是抽过了闻厌手中的烟斗,弯了下唇角:“不过你确实要先还一下债了。”
闻厌直觉这不是什么好话。
他下意识要从对方手中夺回自己的烟斗,然而仅仅是眼神一转,贺峋就已经看出了他想干什么,提前把手一举,十分无耻地仗着身高差欺负人。
闻厌攀着贺峋的肩膀踮脚去够,将要抓到的时候,贺峋就慢条斯理地把手伸直,让他够都够不着。
“你干什么?”闻厌色厉内荏,压下心虚,先发制人地语气强硬道,“还给我。”
贺峋轻笑一声,指尖一转,冰凉的烟杆就抵上了徒弟的下颌。
闻厌被迫顺着对方力道抬起头,后知后觉地有种对方要新账旧账一起算的预感。
“有人好像又不听话,把为师的话当耳旁风了。”贺峋温声细语的,但闻厌不会天真地以为对方此时还在与他说笑。
鉴于这人时不时就要恶趣味地吓他一下,闻厌已经驾轻就熟地掌握了分辨对方话语中细微差别的能力。什么时候是可以不用理会的,什么时候是还可以一拳还回去的,还有什么时候是绝对不能忤逆的……界限分明,成了他几十年间无师自通的一项特殊技能。
现在这种情况就归属于绝对、绝对不能忤逆的范畴中。这意味着对方百年难得一见地捡起了为人师长的责任,对他某件事达到了容忍的阀值,决定要采取些不容置喙的措施。
“厌厌,我说过什么?”
闻厌不敢吭声。
他当然记得刚从兰城出来时,贺峋借万绍之口传的话,让他别总是拿着烟斗。不过当时他正被对方的举动弄得心神不宁,整个人都处于对人微妙的怨怼中,那股反劲一上来,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早就把对方的话扔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样子记得很清楚啊。”贺峋轻笑一声,不紧不慢地把人罪名又往上抬了一级,“明知故犯?”
闻厌秉持着多说多错的原则,继续一言不发,眼神刚往一边偏去,抵在下颌处的烟杆便往上一抬,让此刻他不得不正视着对方的眼睛。
闻厌喉结上下滚动,两种截然相反回答会招来的后果在他心中快速权衡,最终开口道:“没有。”
贺峋挑了挑眉。
……真是个小骗子。
不过今日是能有特例的,小徒弟刚坦明心意,那么乖,那么惹人心动,就算有些不听话还喜欢不老实地抵赖,也让人生不起气来。
贺峋好心地决定再给人一次机会。
他把挑着人下巴的烟管收回来,细长的烟杆被他夹在指尖转了圈,存在感强烈得让人无法忽视,落在闻厌眼中,完完全全是一种人赃并获的意思。
“那这是什么?万绍没告诉你冰月草不能总是用吗?”
闻厌当然知道,可是过去的十年已经让他养成了习惯,一旦闲下来的时候,没了那股清苦的味道就总觉得像少了些什么。
只不过闻厌觉得这个理由听起来不太能够让人满意,于是他估摸着在贺峋那里明面上能过得去的理由,放软了声音道:“头疼。”
不论是真是假,每次他喊疼的时候贺峋大概率都不会为难他了,闻厌主动抬手抱住了贺峋的脖颈,果不其然,对方也伸手揽住了他的腰。闻厌觉得到这种程度的示弱应该差不多了,准备给这场突如其来的诘问画上尾声。
这个念头刚起,头顶就传来一声轻笑。
“厌厌,你疼不疼难道为师会不知道吗?”
僵住。
他最近确实不会头疼了,但对方是怎么知道的?
闻厌在心里闪过某种预感,似乎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对方悄悄做了些什么,但此刻不是深思的时候,他一听这个语气就知道自己说错话,僵硬了一瞬,毫无负担地当机立断改口:“我错了。”
对着捉摸不透的师尊,说我错了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贺峋也早已经习惯了自己徒弟毫无诚意的认错,脸上神情没多大变化。
闻厌又亲了亲眼前人的下巴,见贺峋仍旧微笑着看着他,却没有任何触动,投下来的目光晦暗难明,这才感觉事情可能要糟。
果不其然,下一瞬,身体就腾空而起,竟是直接被人单手一抄抱了起来,闻厌吓了一大跳,连忙紧紧搂住了对方的脖子。
只见贺峋拿着他烟斗的那只手凭空画了几笔,两人身侧的空间顿时传来一阵无形的波动,闻厌顿时认出了对方竟然直接开了传送法阵,立马被其背后潜藏着的意味弄得头皮发麻。
传送法阵开启一次损耗的法力不少,有什么事情是要人专程离开这里做的?
……闻厌不用动脑子都能想得到。
所以他连忙空出一只手来并指一划,另一道魔气就紧随其后打在了贺峋尚未完成的法阵上。
法术相撞,顿时在广云宗的山门旁炸起一阵尘土飞扬,幸好此时大部分修士都在山上的正殿中收拾残局,不然准会惊恐地以为这两位祖宗改了主意又要对仙门下手了。
贺峋简直大开眼界,从未发现自己徒弟竟有如此胆量。
他好气又好笑,偏要继续被打断的传送阵,闻厌自然不肯,短短一会儿功夫就僵持了好几回。
贺峋干脆直接屈腿一顶把人抵在檐柱上,腾出空来制住徒弟不断作乱的手,闻厌坐在对方的大腿上,靠勾着人脖子的手维持住摇摇欲坠的平衡,和人以一种极其复杂扭曲的姿势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