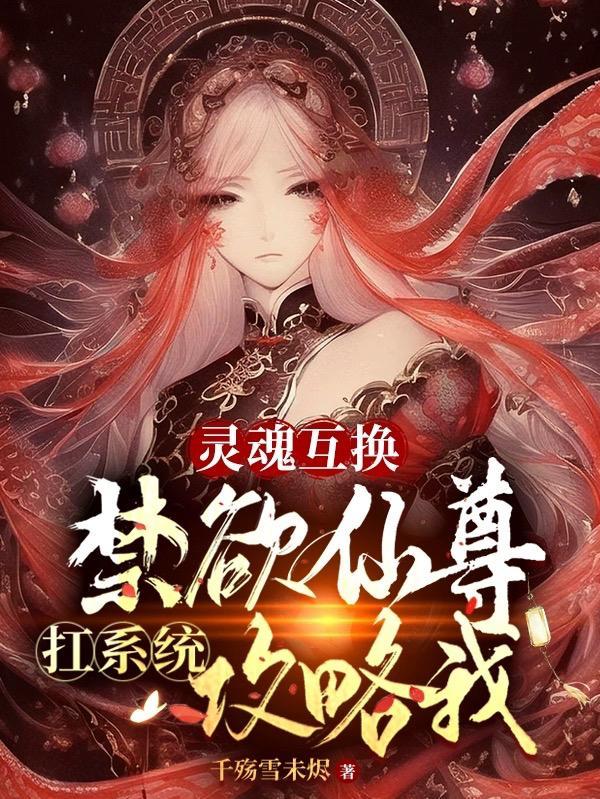布丁阅读>糟糠之妻演员表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他看见之芸穿着男式衬衫,袖子挽得高高的,一把长而蓬松的头发随意地卷起,没有发钗,她居然从厨房拿了一根筷子别上,汗水把流海打湿了全贴在额上,不知怎么的,心情格外地愉悦,弥漫着幸福,仿佛这时光长得再也不会有尽头。
他逗之芸:“小姐,说说话说说话,同志啊,要埋头工作,也要抬头说笑!做人不要像痰孟一样保持沉默,要学会像伟大的马桶能溅起自己的水波!”
之芸笑得蹲到地上,摇着手说:“快把这个人叉出去,成心不叫人干活儿。”
胜寒大笑,许之远也笑,眼光在之芸与胜寒之间飞过来,又飞过去。
空调还未装上,电脑房里十分闷热,十月底的天气,胜寒只穿一件短袖的t恤,汗沿着额角嘀哒往下淌,虽然同样的加班,可是他从不让之芸做一些粗重的活儿,看见她在搬主机便过去接过来。
他们同样裸着的胳膊碰在一起,湿碌碌的。之芸不小心被电线绊了一下,胜寒扶住她。离得这样近,之芸觉得袁胜寒好象一个火炉一般。他扶住她时握住了她的胳膊,那种触感好象变得有实体似的,久久不去。
一直加了半个月的班,才算彻底做完,之芸拿了扫帚拖把,想做一些最后的收尾工作。袁胜寒硬从她的手里夺过了工具,一个人连扫带拖,不一会儿就把诺大的一个教室整理干净了。
几个人约好一块儿去吃饭,胜寒请客。
这一回,胜寒果然不再跟之芸叫板,却坏心眼地撺掇那电脑公司胖胖的小伙子与之芸拼酒。那小伙子大呼小叫,一杯一杯地灌下去,胖胖的脸很快成了一块大红布,之芸不动声色含笑地继续喝,抬起眼时,看见胜寒隔了手上拿着的玻璃,看着她笑。
在胜寒蹲点类思的这段时间里,他和许之远、之芸一起,为类思做了许多的电子课件。他们一伙年青人还隔三差五地一起出去吃饭娱乐。
之芸总是参加的,她发现,每一次她答应了要去,胜寒总是特别地高兴。有一回,之芸故意犹豫着不肯马上答应,偷眼看时,胜寒的眼睁得大大的,满是孩子一般的渴切,之芸忽然就软了心肠,无法把这小小的游戏进行下去,“我肯定去。”她说。
然后她看见胜寒转过脸去,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自己跟自己笑。
之芸也总喊着倩茹与宁颜一同去玩,倩茹似乎兴致不高,往常最爱唱歌的她,变得沉默而恍惚。
宁颜从心底里是想参加这些活动的,尽管在活动中她一贯地安静,但是,那种温洋洋热闹闹的氛围十分吸引她,那让她觉得,自己与普通的年青人是一样的,并不脱节或是疏离。可是去了两次,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之芸私底下问过她,宁颜说:“我妈不让我晚上再出来了。她说,我年纪不小了,总跟一群小孩子混在一处能混出什么讲究来?”
之芸说:“什么话嘛,我不是跟你同岁,你还小着我两个月。年纪不小怎么了,连玩都没有资格了吗?”
宁颜抬头看着之芸朝气勃发的脸,这些天她的小脸越发地黄瘦干涩,才刚立了秋就穿上了厚厚的外套,在背阴地站一小会儿就冷得瑟瑟发抖。她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好象做什么事都没有了资格,只剩下快快把自己嫁出去一件事好做。”
之芸问她:“你和李立平,怎么样了?”
宁颜忽象受了惊吓似地,眉间轻跳一下,摇摇头,再不说话。
之芸搂搂她少女一样薄削的肩,她的快乐并不能传达给她亲近的朋友们。
之芸叹息着说:“你们俩个怎么啦?一个一个的,脸色灰败,蔫蔫儿的,不是都在热恋期吗?这是怎么啦?”
但是,之芸还是快乐的,那种快乐,象春光似的,藏不住,也挡不住。
他们一群年青人去健身馆玩儿,也不知谁先提起的,魏之芸会柔道,他们就去了柔道玩儿,人人换上白色的训练服,看着之芸居然系了一根黑带,有那不服气的男孩子便上来挑战。
在男孩子们统统被之芸摔倒在地之后,胜寒坐不住了,用力扎紧了腰带,站在了之芸的面前。
突然之间,之芸觉得,周围的那些人,那些物,都不在了,只剩下眼前这个大个子,脸上带着笑容的男子,在眼前,有一点傻乎乎的,但是,象一团光,或是一团火,或是一种不知明的热源。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他们纠缠在一处,胜寒的胳膊真的很结实很有力,他们呼出的热气喷在彼此的脸上与耳畔,赤着的脚在垫子上踏出啪啪的节拍。如同急促的心跳。
在最后一刻,之芸觉得,胜寒忽然卸了力,他被她摔得仰面躺在垫子上。在一片乱七八糟的欢呼与口哨声中,胜寒大笑起来。他躺在那里,仰视着那个满脸是汗,精神灼灼的高挑的女孩子。
坏了,袁胜寒想,坏了!
那一次,年青人们玩得太疯,回去的时候,末班公车已经没有了,连出租出十分难打。
袁胜寒与男孩子们分头送女孩子回家。
胜寒故意绕了点儿路,最后送的之芸。
他不知道的是,之芸带他走了回家的最远的一条路。
之芸家的楼道很窄,乱堆了一些纸箱还有冬天腌菜的大缸。
人高马大的胜寒几次被绊,走得跌跌撞撞,之芸低笑:“你怎么了?被我摔残了?”
胜寒咧开嘴笑,黑暗里牙齿特别地白。
到了家门口,之芸掏出钥匙,回头对胜寒说byebye。
胜寒却没有动,忽然俯过身来,下巴磕在之芸的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