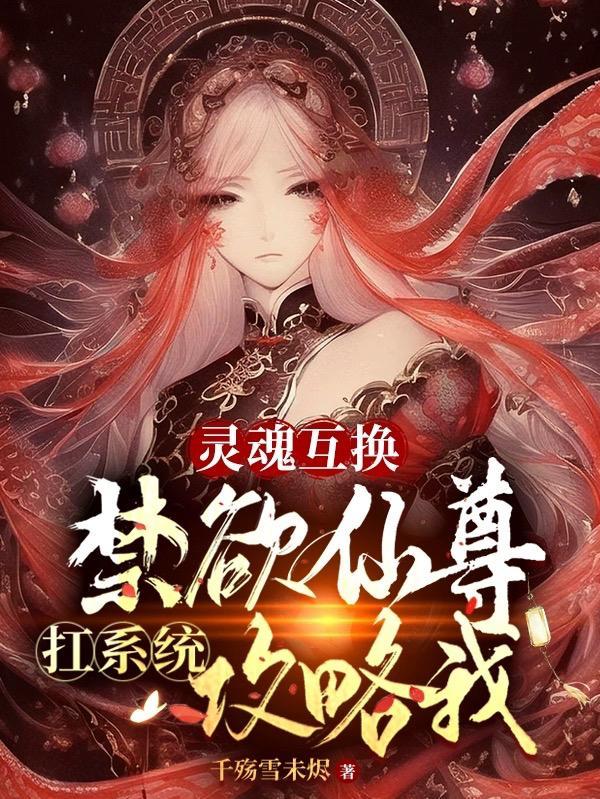布丁阅读>情不自禁下句是什么 > 第90章(第2页)
第90章(第2页)
“军区总医院,”姚宋说着,转头向病房窗户瞥了眼,柔软的病床上,祝琴闭着眼睛,已然沉沉睡去。她说,“阿姨刚睡下,你路上不用太着急。”
火车驶入清市站,又落下阵巨大且持续的噪声。
车门缓缓敞开,像拥挤的沙丁鱼罐头划开道口子,人群喧嚷推搡着涌出,声势浩大。以防止有什么损失,殷燃全程紧握手机和行李箱,被推着走出站台后,她才道了句:“好。”
这么说着,她的脚步却不断加快。
看了眼手表,恰好七点钟。“辛苦你了,我大概半小时后就到。”殷燃保守估计好去朋友那提车的时间,对她说。
“别了,跟我用不着谢,”姚宋说,“阮符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簇拥着上电梯,一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殷燃皱眉,略一沉吟,才回答说:“没。”
阮符那边也好多事需要处理,告知她也不过是徒增烦恼。
按照殷燃的性格,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答案,姚宋“哦”了两声,没做什么评价,只说:“好吧,那你路上注意点就行。”
电话挂断没多久,殷燃提好车开出火车站。
水泄不通显然是一线城市的常事。殷燃皱眉握着方向盘,忽然想到安逸缓慢的鲁南,想到蓟北。
继而,她想到阮符,想到她昨晚没说完的话。盒子里,她上次落下的手链还没还。
道路畅通,后面车主狂按喇叭。殷燃立刻回神。
剩下的几个小时,她连轴转,像个失去情感的永动机。办好住院手续后,殷燃立刻又被带去与主治医师商量下面的治疗计划。
癌症进入晚期时,结果几乎不可逆转。除了普遍才用的放疗化疗,只能进行些不堪大用的姑息性手术,以此来缓解病人的痛苦,尽可能延长几年寿命。
“这个治疗计划怎么选择,主要是看你们家属的意见,毕竟已经是晚期了。”年过半百的医生推推眼镜,翻了翻手中的病历册子,说,“其实手术的话,效用也维持不了太久,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放化疗的。”
见殷燃犹豫不决,医生又道:“不强制要求,你们家属要是觉得还想试试手术,也可以做,不是不能做。”
殷燃点头表示了然,最后说:“谢谢您。我再考虑一下,明天前给您答复。”
医生早已见惯这些谨小慎微,并不在意地点点头,应了声“行”。
推门离开时,他没忍住,感叹了句:“才五十一岁,真可惜了……”
是啊。五十一岁,正是知天命的年纪,人生走过一半,她还未来得及享受什么,就被癌症宣判下死缓。
殷燃握着手中冰凉的病历,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她仿佛在瞬间变得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
消毒水味刺得人鼻酸,怔愣几秒,她的唇角小幅度颤抖起来。她用尽力气咬着口腔中的肉,直到唇舌间舔到铁锈似的腥,才最后勾出一抹难得无比,只勉强可以算作笑的笑。
泪水模糊视线的前一秒,她瞥见手机中的自己,愈发笑得张扬,似乎不再收敛什么情绪,任凭心脏被随意撕烂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