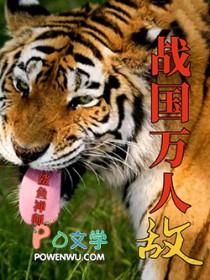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娇养小王妃 鹤归青山 > 第72章(第1页)
第72章(第1页)
温承没有看也知道是谁送来的:“一些旧属,如今不打仗了,闲来无事便去山里打猎,年节时会送些猎物过来。”
“这样啊。”薛映低头看着送来的东西,他记得温承第一次离开京城去的不是漠北,而是关外,他率兵驱逐了觊觎关外的北匈,才前往漠北抵御突厥。
薛映正想着,就见钟贵快步走了进来:“王爷,王妃,陛下亲临。”
薛映没想到兴和帝会亲自来,望向温承,温承安抚道:“没什么事。”他又看向钟贵问道:“还带了什么人?”
“来了几位太医,为陛下诊脉的高太医也来了。”钟贵答道。
自成婚以来,兴和帝便对此事多有疑心,及至后来也在怀疑是否有婴孩存在。温承是清楚的,只不过王府管理严格,平素用的药材都是混着几个方子支领的,熬药的是亲信之人,皆不会泄露出去。只是近来年下,皇亲国戚常须进宫赴宴,薛映皆告了病,想是皇帝始终不得真相,终于无法忍耐,来一探虚实。
按理说装病该躺在寝殿里将养,可如今自己却出现在前殿的书房,浑然没有半点生病的样子,薛映拉住温承的胳膊,问道:“我从后面回去?”
就算是皇帝突然亲临,也不会立时进到府中来,总得给接驾的府里上下留下一些准备的空当,他想着趁这个时候回去。
“无事,”温承圈住薛映的肩膀,将人扶到床边,帮他褪了鞋,“安心躺着便是。”时间虽来得及,他也不想匆匆忙忙间让薛映躲回去。
早年间,先皇在世的时候,只要温承在京里,先皇来便必定会来端王府一次。端王府上下对接驾一事颇为熟悉,可总归没接过这位兴和帝的驾,又是突然而来,一时间虽行动有序,但不免心内惴惴。
待换过衣服,府内上下有职级的属官门皆是站在温承身后,等着陛下亲临。又等了一会儿,兴和帝从正门走了进来。
门外见过礼,步入正殿,兴和帝打量了一圈,笑道:“怎么不见皇婶?”
“劳陛下惦念,内子体弱多病,前阵子拘在寝殿里养着,闷坏了,今日精神刚好一些,便与我在前院中理书,刚又喝了药歇下了。”温承解释道,“不及上前拜见,还请陛下恕罪。”
“唉,皇叔哪里话。朕原是想着召你们到宫中一聚。可宫闱多是女眷,恐是皇叔担心出入不便才再三推拒。”兴和帝叹息道,“还是太后思虑极是,说是我们一家人本就亲厚,皇叔恐也不会见外,皇婶怕是真病了。故而让朕赐几名太医前来诊脉。今日朝中无事,朕来的时候便带了几名太医过来,正好给皇婶瞧瞧。”
说着,几名太医上前躬身行礼,温承看了一眼打头的太医,道:“陛下万金之躯,内子感染风寒之症,若是让冯院正进去,万一过了病气,恐对陛下不虞,还是另命人进去更为妥当。”
兴和帝沉思一瞬,答应了,示意另一名太医进去。
寝殿中,钟贵将大夫迎了进去,走过两层珠帘,大夫待要上前,钟贵将人拦住。
“刘御医是兴和年间入的宫,当年皇后抬举,想必还记得吧。”钟贵轻声道。
“娘娘对我有深恩,没齿难忘。”刘御医勉强笑道。
“你既得沐大恩,该一心报效才是。可我记得,前些年陛下将李妃废为庶人,原是想留她一命,可她却在喝了你的药之后,离开了人世。”钟贵低语道。
刘御医脸色一白,看向钟贵,当年他奉太后命如此行事,原以为没有人知道。可若是此事一发,太后和皇帝皆是容不下自己。钟贵声音依旧很低,问道:“高大夫可知道待会如何呈报陛下?”
刘御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道:“天寒地冻,王妃恐是吹了风,导致风寒症候,又因着饮食不调,致使病症反复,须得仔细调理。”
钟贵满意道:“高大夫所言甚是。”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帘帐后面的薛映都未能听清。方才自皇帝走入殿内,薛映躺在床上,原是有一点紧张,因着温承说了无事,再加上他远远听到兴和帝说话声音平和,故而渐渐放下心来。
不一会儿,高御医与兴和帝回禀,对答果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并与其他御医,一起看了端王府所保存的脉案和药方,议了一回。
兴和帝对这个结果并没有兴趣,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冯院正上前道:“虽是风寒,可是症候反复,恐是有风热之状。”
“你的意思是?”
“也许是王府中有人发烧,传染给了王妃。”
另一名太医道:“前阵子属下去礼郡王府诊脉,侧妃虽是得了风热之症,可脉息却与寻常症状有些不同,臣等商议过,恐是新近出现的一种时疾。”
兴和帝眉头一紧,担忧道:“既是传人,倒是不好,这该如何?”
冯院正上前为君分忧道:“王府上上下下这许多人,很难找出谁第一个传染的王妃,可这病到底传染,若是能排查出一些得过此病的人,对王妃的病,倒是大有裨益。”
“如此甚好。”兴和帝答应着,“那就由你们今日好好为王府的上下人等诊一诊脉象。”
兴和帝开了口,温承没有拒绝,只是命钟贵去传几名管事带着名册过去。几个太医被人接引着,去了旁边一间收拾好的屋子问诊。
温承已然明白兴和帝的用意,心里并没有什么波动。不过今天来问诊的,哪怕看出花来,也找不着真正有孕的人。太医院的那群人再如何医术高明,可他们治病开药一向小心,明面上从来不敢用猛药,若非亲眼得见,一时也想不到竟会真的有男子用了生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