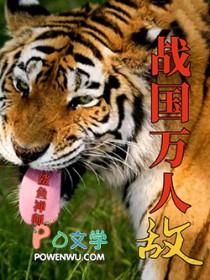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娇养小王妃 鹤归青山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可温承越是这样宽慰他,薛映越觉得心里难过,他想了想,问道:“我是不是该去见一见太后?”
温承隐约猜到薛映为何如此,问道:“你想见她吗?”
薛映自然不想见,但想到那个太监的语气,知道自己若是不去,温承大约会为难,便点点头。
“我想听实话。”温承盯着薛映,望着那双如同静湖一般的眸子敛了一层水汽。
薛映没有说话,似乎是怕泄露自己最真实的情绪,屏住呼吸点了点头。
看出薛映的口是心非和强装镇定,温承在心里叹了口气。在军营中,若是有人在他面前如此,他怕是不会说第二句话。可他很清楚,薛映不是他的下属,不是他的子侄,现在这个情形,说不得骂不得更打不得。
温承见薛映如此,只感无可奈何。
“你与我一样,都是这个王府的主人,想见谁,不想见谁,都按你的心意来。”温承话说得不疾不徐,尽量让薛映感受到安宁。
“这样会不会不好?”薛映担忧道,他不愿意自己牵累温承。
“我的王妃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温承说道。旋即,他看见薛映眼里的水雾落了下来,整个人似乎终于放松下来。
温承揽着薛映,将人抱坐在了自己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后背,让他情绪尽快平静下来。他想,哪怕只是半年前,他都不会想到自己即将和一个小许多的人成亲,他的小妻子情绪敏感,需要时不时地哄着,给他擦眼泪。
温承倒不是觉得麻烦,只是薛映时常这样哭,总是伤身体的。好不容易情况刚稳定下来,又险些哭得喘不动气。
将人安慰的差不多了,温承注意到薛映看上去一脸疲累,便道:“想吃什么?”
“我不想吃饭,想睡觉。”薛映嗡里嗡气地说道。
“那便先睡吧,若是晚上饿了,让他们送饭过来。”温承直接将人抱起来,放到了不远处的床上,帮他盖好被子。在床前守了一会儿,见薛映彻底陷入沉睡,他才走出房间,唤来钟贵。
“下午太后遣人到了王府,王妃恰好去了会客厅,正好听见了他嚼的舌根子。”钟贵出门后便去问了嬷嬷们,已然获知下午之事。
温承冷笑一声。
“王妃现在无法操劳,那过段时日,若是宫里再过来人请他进宫学规矩,该如何?”钟贵问道。
“不必学这些,他随意就好。”温承道。
“是。”钟贵忙应下。
“我今日瞧见忠勇伯府送贺礼了?”温承问道。
“正是呢。他们家在京中鲜少与人来往,这次竟然上门了,莫不是他和王妃有些渊源?”钟贵问道。
“同族,不过是远亲。”温承命人调查薛映的事情,下属便调查了个一清二楚,这让人很容易想起一桩往事,先帝最属意的儿子并不是当今皇帝,而是他的哥哥,正是忠勇伯府出身的薛贵妃之子。只是那位皇子自小病弱,后来一病没了,才轮到现在的皇帝幼年登基。
今上亲政之后,众人清楚局势,便都远着忠勇伯府,不再往来。
历来办喜事,来者都是客,钟贵虽知道忠勇伯府情形特殊,并没有特别对待,却不防薛映与他们有一层远亲的关系,着实微妙。今次见王爷特意提起,他忙问道:“那这贺礼咱们是收着呢,还是退回去?”
这几年为了与皇帝达成一个表面上的平静,温承鲜少与人结交,哪怕是他举荐入京的官员,亦不再来往。同样的,他也不管皇帝与谁交好。这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默契。
温承心里清楚,他打杨文景的举动,无疑会让皇帝恼怒。一则敬国公府在朝中并无权势,仰仗的都是皇帝的宠信,打狗还要看主人。二则在外人看来,自己与薛映在这之前并没有任何往来。故而今天下午虽是太后派人出面,想是皇帝背后授意。加之皇帝应当知道了与忠勇伯府的这一层关系,只怕更加疑心。
忠勇伯薛怀玮已过古稀之年,是个很有见识的人,数年蛰伏家中,与子侄低调度日。此番瞧见时机,便抓住机会前来赠礼,算来每一个省事的。
既然他们闹得自己王妃不快,温承很快做出决定:“收着。着人去忠勇伯府传话,若是府上有老家的厨子,送一个过来。”皇帝觉得自己羽翼渐丰,该收回自己的权力,他这位做皇叔的,看在先皇的面子上,愿意让出这些年的权柄,但这并不代表他能一退再退,全无底线。
“是。”钟贵忙答应着,命人赶紧去办。
温承站在檐下,继续思忖着。薛映和孩子的事情,能对邓如铭与温敛等人透个底,因着他们心中有数,了解其中轻重,并不会与旁人说。至于其他人,只等日后孩子平安出世,才能让外人知晓。否则,若是提前说了,搞不好又弄出一堆新的流言,也会让人虎视眈眈。
虽说大夫们反复强调,有孕之人情绪敏感,可温承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情毒是几百年前出现的毒药,几经变化,成了现在的药效,也许还有隐藏的不当之处,尚且没有被发现。
温承想着让人去别处寻找古籍,安排妥当之后,他拿起桌子上的册子,看起婚礼准备的如何了。婚期将近,一切该紧着些了。而明日一早,他会去一次皇陵,告祭先祖自己将要成婚一事。
大婚的日子很快到来,两人的婚礼并没有刻意作嫁娶之礼,不需要送亲迎亲,薛映仍旧住在府里,并没有搬出去。待到成亲当日,他没有早起,而是与平常一般用过早饭后,才在众人的帮助下换上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