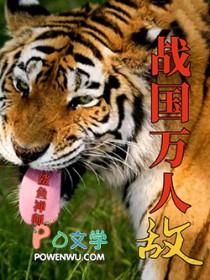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偏执美人绝症后想开了苏清词 > 第31节(第2页)
第31节(第2页)
苏清词往后躲开,自己脱掉外套,没来得及下步动作就被裴景臣抢走,挂到一旁的衣架上。
苏清词有点想笑,但是笑不出来。好像一个镜像的世界啊,从前都是他屁颠屁颠迎出门口,对裴景臣说回来了?然后主动接过他手里的东西,再帮他拿外套,挂外套。
现在全然对调了。
仿佛从他在ICU醒来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颠倒了。
苏清词牛鬼蛇神的想,会不会自己其实还在ICU的病床上深度昏迷着,现在所见都是幻觉,都是梦一场。又或者,自己其实早就死了。
裴景臣把拖鞋放地上,让苏清词换。苏清词从天马行空的幻想中挣脱出来,躲开裴景臣下意识的搀扶,像只小仓鼠似的溜边儿走。
裴景臣莫名忍俊不禁:“去哪儿了,怎么不坐轮椅,累着怎么办?”
苏清词语气凉凉的:“不想坐。”
裴景臣不是想偷看,而是自然而然的动作——低头瞄一眼购物袋里的东西,心想他昨天买了很多,罗列的清单在手机文档里堆了两千多字符,按理说不该有遗漏的东西需要苏清词再去买……
咖啡豆?!
裴景臣神色一紧,开口不是训斥也不是说教,而是平平无奇的:“要喝水吗?”
裴景臣嘴上问着,手里也做着,倒了杯温开水放茶几上。
苏清词没喝,咽了咽干涩的喉咙:“你在大扫除?”
裴景臣点头:“嗯。”
苏清词不知该说什么好,因为槽点实在太多,吐槽不过来了。他把头枕上靠枕,靠枕散发着薰衣草洗液的清香味,是裴景臣洗后并晒干的。
苏清词不想发脾气,也没力气争辩,他深吸口气道:“我昨天说什么来着?”
裴景臣薄唇轻启,目光闪烁:“我们分手了,扯平了。”
苏清词冷笑:“原来你不聋啊。”
裴景臣摘下套袖:“你还说,我们什么都不是,你拿什么身份什么理由照顾我?”
苏清词很满意裴景臣的记忆力,免去了他再重复一遍的辛苦:“一字不差。”
苏清词直视裴景臣,眼底浸着不近人情的凉意:“你没有答案,所以我让你滚蛋。”
裴景臣反而笑了:“我今天来了,因为我有答案了。”
苏清词怔了下,下意识追问:“什么?”
裴景臣:“我以你前男友的身份照顾你。”
苏清词目瞪口呆,他真有点不认识裴景臣了:“凭什么?”
苏清词说:“理由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凭什么要照顾我,我又凭什么要被你照顾?”
苏清词从来都不是个宽容有耐心的人,他的温柔全给了裴景臣,也只给裴景臣。对外人包括安娜丽丝在内,尖酸刻薄,赤口毒舌,咄咄逼人。
裴景臣暗嘲自己大概是被苏清词惯坏了,从未领略过小少爷真正的脾气。现在体会到了,还真是不留余地,刻骨灼心。
苏清词上回这样质问他,正是他给薇薇安画肖像那天。裴景臣到小区外面等,他们站在路灯下,飘雪中,苏清词穿着深色的羽绒服,映的瞳孔愈发的浓黑深邃,鼻尖被冻得通红,面容泛着惊心动魂的苍白,他说:“你是在气我言而无信,还是吃醋我笔下画了别人?”
一句话,裴景臣做了三天噩梦。
三天后他明白了,确信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气势汹汹跑去找苏清词顾左右而言他还东拉西扯的根本原因——兴师问罪。
他真的吃醋了。
吃醋苏清词“背叛”了自己,明明说过眼里只有他,却一扭脸就画了别人。
其实他没资格管苏清词画谁,无论画薇薇安是因为工作,还是单纯友情相赠,他都无权干涉。
但是裴景臣控制不住,心里好像有根刺,拔不出来,放任不管又越扎越深,终有一日会腐烂化脓。裴景臣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有这么强的嫉妒心和占有欲。他嫉妒薇薇安,吃醋这个突然跑出来轻而易举打破苏清词规矩的女人,他想自私的占有苏清词的画笔,让苏清词在绘制人像这个领域内只有他,只画他。
裴景臣曾反感苏清词的善妒和占有欲,如今自己嫉妒起来,也不比苏清词逊色多少。这不是同样的无理取闹,敏感偏激吗?
嫉妒的前提是在意,裴景臣承认自己在意苏清词,毕竟年少相识,又同居了三年之久,就算是合租的室友也会有感情的。苏清词说过只画他,所以他深信不疑,并理所当然的认可了这个“规矩”,而苏清词打破规矩,他难以接受而已。
迷茫中的裴景臣是这样分析的。
直到从韩国签约回来,他得知苏清词进了ICU。他没想到自己的反应会那么大,天崩地裂,浑身发冷,夜不能寐,如坠深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体里硬生生剥离,是小说和影视剧里惯常说的灵魂吗?
裴景臣不知道,也不敢回想那种恐怖到了极点、说一句痛不欲生也不为过的感觉。
苏清词醒来时,他欣喜欲狂又措手不及,快要枯死的心脏因为紧张苏清词会说什么话而鲜活的跳动起来。
原来,苏清词早已在他心底生根发芽,嫩芽活着,他心脏蓬勃,嫩芽枯萎,他心脏干涸。至于嫩芽长成,结出了怎样壮阔的大树,裴景臣难以估算。而当苏清词说出那句分手了,扯平了的时候,裴景臣终于肯定——绝不是干干瘦瘦的小树苗。
尤其是那句……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是,是从曾经说出“我要永永远远的纠缠你”的人口中说出来的。
*
所以,你凭什么要照顾我?
裴景臣蹲到苏清词身前,目光炯炯的看着他:“就凭,我想继续被你纠缠。”
苏清词觉得自己幻听了。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