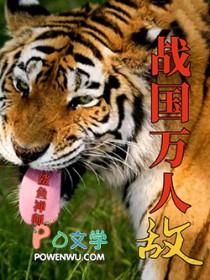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女仵作洗冤录好看吗 > 第62章(第1页)
第62章(第1页)
雷鸣亦叹道:“这些举子怎麽看着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只有江瑟瑟沉默不语,费平见状,便问:“江姑娘在想什麽?”
江瑟瑟看向费平,道:“我总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费平道:“我也觉着不对劲儿,可又说不出名堂来。好在他人没事儿,我们回去也好交差,至于剩下的,慢慢查呗。”
“你们打算怎麽查?”雷鸣笑道,“改天儿从水里拘个鬼出来问问?”
费平哑然。
江瑟瑟也没理出头绪来,无奈道:“回去再说吧。”
乌夜啼(七)
江瑟瑟与费平回到京兆府后,发现裴霁舟与蔡宏同坐堂内品茶。对于这位裴郡王隔三差五地造访,费平已经习以为常,他向二人揖礼后,便将事情经过细述了一遍。
其它倒没什麽,只是蔡宏在听到江瑟瑟做主找人“做法驱鬼”一事,颇为在意,他放下手中的茶盏,担忧道:“就怕百姓信以为真,以后一有病症只找道法,不去就医啊。”
裴霁舟看了江瑟瑟一眼,道:“本王虽未亲眼见着那人,可听尔等描述,亦知他是被心病所困,瑟瑟对症下药并无不妥,不过蔡大人之虑也非空穴来风。依本王看,眼下最紧要的还是要先摸清曲江乌夜惊现离奇啼哭一事的缘由,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此事。”
蔡宏颔首称是,随即便下令由费平负责查办此案。
“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蔡大人尽管直言。”裴霁舟又补充道。
蔡宏先道了声谢,后又道:“就这点儿小事,下官还没脸寻求王爷的协助。”
裴霁舟道了声“无妨”,随后看向江瑟瑟,蔡宏眼珠子一转,连忙声道道:“王爷请恕下官有事不能奉陪了。”
裴霁舟点头,蔡宏提着衣摆一溜烟儿地跑出了屋子。
“王爷最近好似閑得很?”屋中突然只剩下他们两人,江瑟瑟不知该说些什麽。
裴霁舟神色微滞,心虚回道:“倒也不是那麽閑,平日里晨晚会去练会儿兵,就中午时分空閑些。”
听裴霁舟这语气,江瑟瑟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的问话似乎有揶揄之意,她忙解释道:“我非是责问王爷的意思,只是觉着王爷也不在京兆府当值,也未奉圣令督察,总是朝着这边跑,会给人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
说完,江瑟瑟又后悔得咋舌,怎麽这解释有种越描越黑之感。
裴霁舟亦是被噎得好半天没说出话来,顿了许久之后,才弱弱辩解:“我也没有每天都来”
江瑟瑟干笑着不敢再多说。
两人之间又沉默了一会儿后,裴霁舟主动问起今日之事,“能过你的观察,你觉得何首文落水一事,人为的可能性有多大?”
江瑟瑟思考后谨慎答道:“十有八九。”
“哦?”裴霁舟讶然,“竟这般肯定?”
江瑟瑟点头,“何首文这人的人缘很差,可能与他自性性格有关。”
“怎麽讲?”裴霁舟问。
江瑟瑟解释道:“我从老刘的口中得知,他昏睡了一整夜,期间除了老刘帮忙张罗着请了大夫并细心照顾外,竟无一人去探望关心他。即便我们去了之后,别的考生也只是好奇地围在屋外看。且当何首文醒后,从他的言行来看,此人自负又自私,得罪的人应该不少。”
“这麽一说倒也通了。”裴霁舟道,“别的考生也只是听到的夜啼,可无人像他那样受到了实质性伤害。想来,应是有人借机报複。”
江瑟瑟点头,表示认同裴霁舟的看法,“但我只是一小小仵作,除非府尹大人吩咐,无权插手调查此事。不过这起案子也不複杂,费参军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应该很快就能查出结果。”
江瑟瑟未料到的是,她把话说得太满了。因为事情过去了两天,费平却还没有纠出幕后之人。不但如此,那天被带去聚贤楼的术士出来后便将自己的所为大肆宣扬了一番,加上曲江夜啼一事传得沸沸扬扬,心中害怕的百姓纷纷慕名去找那术士做法护身,短短两天,他就已赚得盆满钵满。
就连恪王府的忠伯也跟风买了几包药回去撒在了王府四周。
“忠伯,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裴霁舟气道,“你曾也是个行军打仗之人,怎地如今也信起这歪门邪道来了。”
忠伯看着手中仅剩的半包药粉,拍着脑袋懊悔道:“糊涂啊,王爷教训得对,老奴还真是老糊涂了。”说罢,连忙将手中的烫手山芋甩至一旁。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衆人预料,裴霁舟担心祸及到江瑟瑟身上,于是亲自将那个术士抓了个人赃并获。
那术士还辩称:“王爷,我这可都是正经生意啊。朝廷每年都还讲禅论道,摆道场祭天地呢,你敢说那也是歪门邪道?”
“你这厮休得诡辩!”仇不言指着那人怒斥道。
裴霁舟按下仇不言的手,上前一步道:“佛法道家乃先辈留下来的传统,礼佛传道亦是正法行径,朝廷从未禁止任何人行此事。而你行的又是哪门法哪门道?你所卖之药当真能除魔驱邪治百病?分明是你借机敛财,强行混为一谈。”
“诶诶诶,王爷明鑒,治百病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术士继续狡辩道,“是大家用了我的药后发现有效果口口相传来的。至于能不能驱邪,王爷,您可如何能证明不能驱呢?”
“你这巧舌如簧的口才,不去做讼师,只做个街头术士倒也屈才了。”裴霁舟都被那人气笑了,他道,“本王没法证明你的药不能驱邪,但本王却知你是无证行医,兜售假药。你也别再也与本王逞口舌之争,是与不是一查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