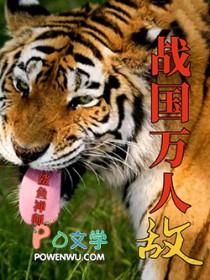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竟是吾妻最新更新章节免费阅读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岁洱觉得邱意婉的袋子比她的大,邱意婉觉得岁洱的袋子比她的好看,两人时常会因此唇枪舌战。
但最后倒霉的永远是岁崇,即便他现在失忆了——
邱意婉和岁洱皆是愤愤不平,同时回头,同时委屈埋怨地瞪了岁崇一眼。
岁崇:“……”
岁崇不明就里,却又莫名其妙地不敢多言,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我来挖吧。”说着便朝着邱意婉走了过去,将岁岁交给她的同时,接过了她手中的铁锹,转而就将其中一把铁锹递给了岁洱,“给,挖。”
言简意赅两个字,丝毫没把岁洱当外人。
岁洱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没好气地接过了铁锹,开始和她哥一起挖起了压在尸体上面的小山包。
好人当到底,送佛送到西,兄妹俩决定干脆直接将这条路给修通,于是便跳到了高高的小土山顶端,一锹一锹地往旁侧的悬崖外抛。
黄泥土伴随着石块一同跌落进了湍急的河流中。
兄妹俩一刻不停地铲了将近一个时辰,浑身上下皆被雨水打了个湿透,终于将挡在路中央的那座土山给清理干净了,仅留下了一小堆石土做坟堆用。
那具尸体的全相也彻底暴露在了众人眼前,确实是被重物砸死的,整个上半身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滩烂泥。
邱意婉一手打着伞,一手抱着孩子,也腾不出第三只手去帮忙,只好对岁崇说道:“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辨明身份的遗物。”
岁崇点头,蹲在了那具尸体旁边,最终在看起来像是脖子的位置发现了一串沾满了血泥的项链。
是一串很简约的项链,黑色编绳上穿着三颗小圆石头,左边那颗蓝色的石头上刻着“爹爹”二字,中间那颗粉色的石头上刻着“妞妞”,右边那颗黄色的石头上刻着“娘亲”。
所有的字体皆是歪歪扭扭,一看便知是出自垂髫小儿之手。
岁崇长长地叹了口气,握着项链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家三口,女儿可能也就四五岁大,刚识字的年纪。”
邱意婉悲哀道:“真是可怜她们母女了。”这种感觉,她真是能够感同身受。
岁崇和岁洱一同将这个男人埋在了路边,用木板简单地在坟前立了个碑,将那串项
链牢牢地系在了碑上,以便他的家眷日后来寻。
给亡者鞠了三个躬后,一家四口继续启程上路。
岁崇和岁洱的头发衣服全湿透了,邱意婉担心他们俩着凉,就问俩人要不要先换身衣服?结果兄妹俩却都摇了摇头。
岁崇的理由是:“不确定前面还有什么,先这么走着吧。”他手里还拎着那把沾满了泥污的铁锹,太脏了没法儿重新放回海纳袋中。
岁洱的手里也拎着铁锹,即便淋着雨也依旧是活蹦乱跳:“我们狼族本就生在北境严寒之地,才不怕风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岁洱的话风忽然一转,抬起左手摸了摸自己的红发,“这染发膏还真挺厉害的,下这么大雨都没掉色。”
邱意婉忍俊不禁,忽然间,她握在左手中的那柄伞被岁崇接去了:“我来吧。”他浑身湿透,又沾满了泥土,不敢靠她太近,担心会蹭湿蹭脏她干净的衣服,却又担心雨会淋到她和孩子,打伞的那只胳膊几乎伸了个笔直,将她们母子俩尽数挡在了伞下,自己却全然暴露在了雨幕中。
邱意婉抱孩子的那只手臂确实有些酸了,立即将岁岁换到了另外一只手中,又朝着岁崇无奈一笑:“郎君为何自己不进到伞底下?”
岁崇神不改色,言简意赅:“伞不够大。”
邱意婉红唇一瘪,满目伤心:“看来郎君是嫌弃人家胖,占地方了?”
岁崇:“当然不是!”
邱意婉:“那郎君为何不愿与我同执一把伞?”
岁崇无计可施,只好靠她近了一些,却依旧有半个身子淋在雨里。
邱意婉也没再强迫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心道:这都多久了?什么时候才能够主动和人家亲近亲近呀?女人都是需要呵护的!
又继续前进了一个多时辰,一家四口终于抵达了位于半山腰处的石雕村。
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石雕村的现状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繁华,村口空空荡荡,人烟稀少;村前的地面上落满了凌乱的枝叶,显然已多日无人打扫,甚至连来往的车痕和脚印都没有。
目之所及之处的唯一活人,就是那位坐在村口大树下的老人。
老人头戴蓑帽,没穿簑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手中却又打着一把大伞,伞底的空间容纳两个人都绰绰有余。
更奇怪的是,老人的蓑帽前竟然还垂挡着一面薄薄的白纱,更令人看不清他的真容。
配合着灰暗的天色,这一切看起来都有些诡异阴森。
空气还阴凉凉的。
岁洱摸了摸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的后脖子:“我、我怎么没听到他呼吸啊?他不会、是一尊石雕吧?”
邱意婉和岁崇也都有些拿不准主意。没有明显呼吸声,却又散发着活人的气息。
正在这时,那位老人忽然僵硬地扭动了脖子,将被遮挡在白纱后方的视线投向了他们一家四口,嗓音低沉又粗哑,像是十几年没说过话似的:“你们怎么来的?”
一句无波无澜没有情绪的话,听不太出语气,也看不清楚表情,所以不确定他到底是在诧异还是在平常询问。
岁洱回了句:“下着这么大的雨,我们还能坐马车么?肯定是自己走过来的呀!”
老人又问:“路不是断了么?”依旧是听不出语气和情绪的低沉粗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