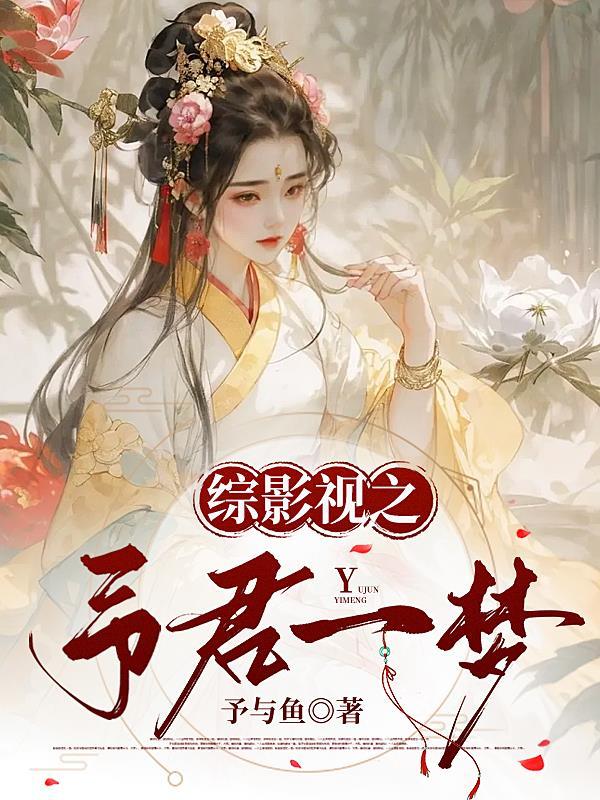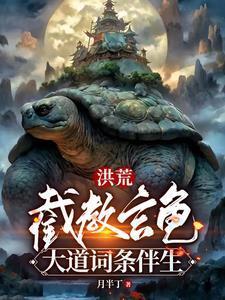布丁阅读>唐朝一书生 > 第22章 清廉度使(第1页)
第22章 清廉度使(第1页)
唐末颍上县城,不在颍水边上的润河镇,而在颍河河畔的慎城镇。
清晨。
颍上县令郑乾,早早候于馆舍,身后站着诸多士子。
苏皓在那等得直打哈欠,心中对节度使腹诽不已,若非族长和亲爹再三训诫,他才懒得陪这个“蠢货”浪费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杂役打开大门,宣武军节度使陈远(随便编的,874年颖州属于宣武军管辖,节度是不知道叫啥,883年朱温成了宣武军节度使)踱步走出,身后只跟着一个中年仆从。
主仆二人,皆衣着简朴,浑身上下都彰显着什么叫清廉。“惭愧,惭愧,让诸位久等了。”陈远抱拳笑道。
县令郑乾立即上前,赔笑讨好道:“陈公莫要自责,只怪我等来得早。”
“见过陈公。”众士子纷纷行礼。
陈远捋着胡须,抬眼一扫,微笑颔首:“县中俊才,今日似又多了几个。”
郑乾连忙介绍新面孔:“此为本县举子刘风,字子贤。”
刘风拱手作揖:“晚辈见过陈公。”
陈远见此人穿戴虽普通,腰间玉佩却价值不菲,一看便知出自地方大族。他的笑容愈发亲切和蔼,拉着刘风的手说:“子贤一表人才,如此年轻便已中举,他日定为国之栋梁!”
“陈公谬赞,晚辈愧不敢当。”刘风谦虚道。
一番掰扯,郑乾又介绍:“此为本县廪生张明……”
“可是文靖公(张九龄)之后?”陈远连忙问道。
张明难掩脸上的自豪,拱手说:“后进末学,拜见陈公。”
陈远顿时又拉手鼓励:“文靖公乃一代贤相,尔当努力向学,不可坠了先祖之名。”
张九龄以直言敢谏、风度翩翩著称,为开元盛世的缔造立下汗马功劳,被后世视为贤相典范。
作为张九龄的后代,张明连忙说:“前辈敦敦教诲,犹如洪钟大吕,晚辈万万不敢或忘。”
这套虚伪把戏,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苏皓站在馆舍大门前,很想一剑把节度使砍了。磨磨唧唧,沽名钓誉,让人直犯恶心!
两天前,苏皓在祖宅,也是这样被陈远拉着手。当时还有些受宠若惊,但他很快就发现,只要是出身大族的士子,都要被陈远拉手扯上半天。
再仔细一打听,好家伙,朝堂新贵啊。
去年的河南节度使叫王宏,此君远离长安,不知朝政变故。竟把狄仁杰、姚崇请出贤良祠,把大宦官田令孜的塑像搬进去,河南贤良祠摇身变成田公公的生祠。
糊涂蛋一个,结局可想而知。左散骑常侍李义府,随即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还没出京就遭弹劾罢免。
右散骑常侍赵德言,接任河南节度使的职务。这位好歹离开长安了,只可惜走在半路上,莫名其妙又遭弹劾罢免。
陈远这个家伙,自己担任吏部郎中,他的老师是尚书左仆射郑畋,郑畋为人正直,心系社稷。
僖宗扳倒田令孜之后,郑畋参与东都洛阳的官员考核事务,陈远参与统计全国官员信息。统计工作结束,陈远连升八级,一跃变成宗正寺卿!这都还不满意,生生干翻两个散骑常侍,如愿以偿跑到河南做节度使。
知县亲自充当导游,一众士子全程陪同,后面还跟着士子们的大量仆从。再加上差役开道断后,队伍竟绵延二三里。
将节度使老爷引至一民巷,县令郑乾指着矮亭说:“陈公,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崇德坊。”
陈远连忙端正衣冠,上前查看亭匾,惊喜道:“果为颜鲁公亲笔,吾当拜之!”
颜真卿书法精妙,以楷书和行书闻名于世,其书法风格端庄雄伟,气势开张,世称“颜体”。
陈远提起衣摆跪下,对着颜真卿的题字长跪,身后士子也只能跟着大拜。
跪拜一番,陈远起身欲走,却见亭边有块石碑,石碑上还刻着一棵青菜。
陈远皱眉问道:“此乃颜鲁公题名之亭坊,何人竟敢擅自立碑于斯?”郑乾回答:“前任知县所为。”
“拆了!”陈远喝道。
郑乾连忙低声提醒:“陈公,不便拆除,否则必然引起民愤。”
陈远愣了愣,只得说道:“细细讲来。”
郑乾解释说:“十年前,颍上大灾,饥荒遍地,又逢加派军饷。当时,颍上百姓只剩两万人,加派的军饷就有三万贯。知县赵怀仁刻青菜碑,题‘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于碑上。他与官吏同吃杂粮、同饮菜汤,劝导大族放粮济民,如此保得一方平安。”
陈远瞬间沉默,不知如何言语,这里头的水有点深啊!
颍上县商贸发达,怎么可能只剩两万人?定有无数百姓,托庇于士绅豪族,不在官府的户籍黄册显示。
至于劝导大族放粮济民?怕是当时刀光剑影,知县用了雷霆手段!
陈远盯着青菜碑的落款,仔细回忆赵怀仁此人信息,很快拍手笑道:“原来是赵主簿,不料他竟有如此政绩。”
郑乾惊讶道:“赵知县做主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