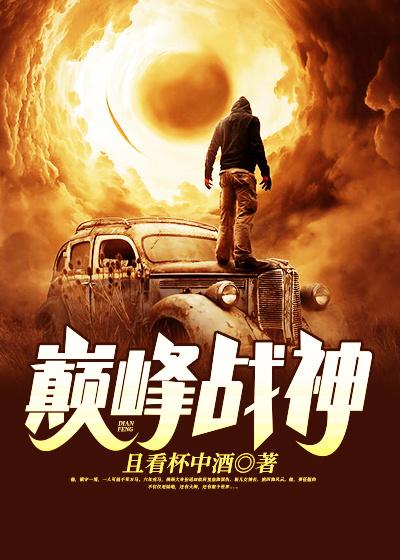布丁阅读>天意可违by迟归鹤笔趣阁 > 第七十八章(第1页)
第七十八章(第1页)
萧琢比萧恪要大上十多岁,也是兄弟最像父亲的一个,身形比弟弟健壮了不止一星半点,拎起人来跟老鹰逮小鸡崽似的就把人抓到了自己面前。
不过那记拳头被贺绥拦了下来,趁着这个空挡,白子骞赶紧上前把人拉开到一边坐下。
“成玉,稍安勿躁。都是自家人,别闹得不痛快了。”
萧琢看了眼白子骞,重重叹了口气跟着坐在一边。不过并没有立刻同萧恪说什么,而是同贺牧与白子骞夫妇提起要粮一事。
被安北节度使府上人那话挤兑的事他没有在几人面前提起,只是如实告知粮草贻误之事。
贺绥在旁听着一直皱眉,听到后面不由扭头看了眼萧恪。前些日子,他在溪吾书斋时知晓萧恪提前备下粮草之事,当时说是猜测,却不想这才多久就已经应验了。
“那眼下……”
几人互相瞧了眼,说心中不愁也是假话。
冬日北境粮食匮乏,他们即便手中还有现银预留,怕也不好将百姓手里的粮米都买光。可若是不解决,这数万大军扎营驻守总不可能饿肚子。
贺绥见状,同萧恪交换了个眼神。
萧恪点了点头,他备下的粮草本就已由魏家兄弟经手运至附近州府,原本为的就是解燃眉之急,到不在乎这功劳由谁来说。
贺绥心中有数,开口道:“粮草之事,有法子解决。”
那三人听后愣了一下,贺牧看向弟弟询问道:“阿绥有办法?”
但贺绥却摇了摇头,直言道:“并非是我。而是允宁事先便料到会有此情况,故而早早留下后手,此刻粮草正在运来晋阳城的路上。”
他只说了一两句,将萧恪前些时日的苦心绸缪点得清清楚楚。
萧恪听了却叹了口气,他无意居功,所以刚刚才没有开口。贺绥惦念将士和长姐困境,没忍住便说了,还特意提了是萧恪的周密安排。
贺牧脸色有所缓和,看向萧恪的眼神也有些耐人寻味。
倒是一旁的萧琢阴着脸追问道:“三弟是如何提前预料的?”
“大哥不信我?”
“事有蹊跷,不得不多问一句。”
被亲大哥怀疑,萧恪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即便已重活一世,自以为心足够冷了,可面对血亲猜忌责问时仍会觉得心里堵得慌,一时便有些难开口。
贺绥这时伸手过来覆在萧恪手背上,抬头直视萧琢,认真说道:“萧大哥。若是允宁真有害人之心,他就不会费尽周折运来粮草。至于为何筹粮,允宁早早同我说过,是因为朝中有人通敌卖国,意图内外联合剿灭北境大军。”
另外三人听后顿时神色一凛。
“是何人?”
萧恪摇头,坦然言明不知,弄得几人都听懵了。
“我只能肯定有人通敌,但时日尚短,究竟幕后之人是谁,我还没有摸出来。”萧恪能肯定是因为有前世的记忆为证,但这人藏得极深,他从前并未用心琢磨过,是而死时也不知晓这人身份。
毕竟是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白子骞沉思片刻开口问道:“那允宁是如何断定朝中有人行此悖逆之事?”
“猜测。但我已有些头绪,只是心中还有些许疑惑之处,此次来也是为了解我心中困惑。”
“你说。”
“我和阿绥曾在京中见过一北燕人。他说自己是寻常商贾,但我瞧此人行事颇为剽悍,且有些胆识谋算,绝非寻常人。而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时曾有一北燕人向这商贾行礼,我觉得那礼节意味不凡,只是苦于身边无人可问。”
萧恪提起龚野,他起身学着记忆中见到的那北燕人的动作,将左手按在肩上,微微垂首。
白子骞脸色一变,忙追问道:“允宁,你确定是这个动作?”
萧恪点了点头,贺绥也在一边证实道:“我当日也在,同允宁学得一样,只是当日那人拇指是向手心勾起的,余下四指约莫正好按在肩头处。”
“夫人。”有了贺绥的补充,白子骞心中留更笃定了,他不由看向自家夫人。
贺牧脸色阴沉,显然已心中有数。
贺绥有些担忧地开口:“长姐,此礼节到底有何意义?”
“这是…对北燕王族行的礼节。”
北燕王族出现在京中,甚至还特意见过萧恪他们,此刻不必再多说些什么证明,贺牧他们也都信了方才的通敌之说。
白子骞跟着追问那北燕人的相貌,萧恪也一一答了。
“他倒是通报了姓名,但既是北燕王族,想来这‘龚野’的名讳也必然是胡诌的。”
萧琢本来一直沉默不语,在听到亲弟弟的描述后,沉思了下突然开口道:“我倒是突然想起来一个人。北燕王室…长相又如靖之一般并不太像北燕人……父王还在时同我提过,北燕汗王曾纳过一个齐国女子,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不过北燕看中血脉关系,排斥异族女子所出之子,若是猜得不差,八成便该是这人。”
白子骞闻言颔首表示赞同,反倒是萧恪皱起了眉头。
龚野曾多次表露出对贺绥的招揽之心,可在萧恪的记忆中,分明对龚野这个人没有半点印象,更不要提贺绥今生尚没有征战沙场,远不该惹得北燕人那般主动。
而前世贺绥被陷害通敌也是七八年之后的事了……先前种种异样在脑海中回忆起来,萧恪突然萌生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念头。
既然他能重活一世,是不是代表冥冥之中有人同他一样……也是历经前世而来。
许是他神情过于凝重了,教贺绥扭头正好瞧见,便唤了一声,“允宁,你怎么了?脸色这样难看……”
萧恪摇摇头,只说是听完龚野的身份有些震惊。毕竟和旁人一起重活一世这种怪力乱神的话说出口,难免有些惊世骇俗了,他还没有想好解释的理由,便只能继续瞒着。
自怀中取出一枚铜符,交予贺牧,一边交待道:“这是我的令符。押送粮草的是两个魏姓少年,他们只认牌子不认人,牧姐届时去晋阳城中的广源米行找他们兄弟二人即可。”
一枚小小的铜符关系着十几万大军入冬前的生计,贺牧攥着那牌子只觉有千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