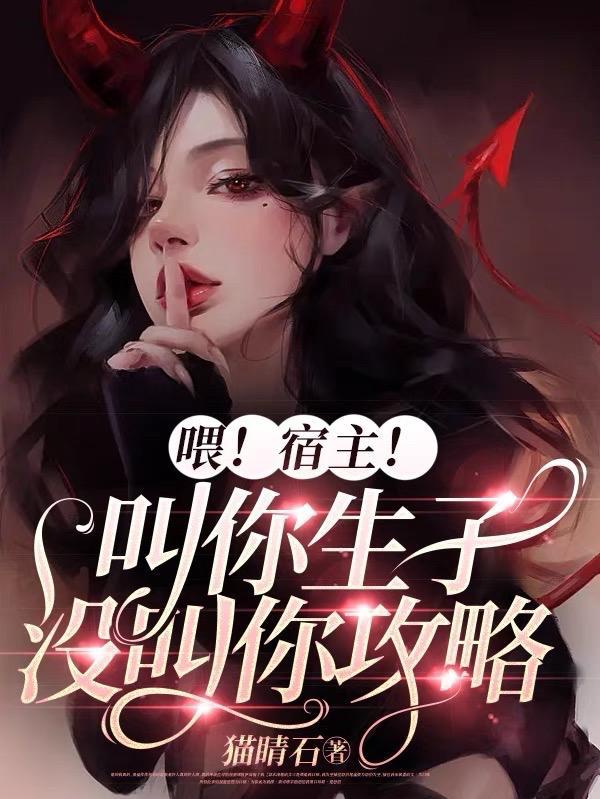布丁阅读>大明 从假太监开始 > 第19章 靖难(第1页)
第19章 靖难(第1页)
朱瞻基正欲再说些什么时,房门再度开启,一名侍女走进来,见了朱瞻基便施礼道:“老爷请您进太孙殿下过去。”
朱瞻基听罢点头,知是金忠已醒,遂推门而入。
室内热气腾腾,金忠脸色苍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半日未见,他竟成了这般模样。
朱瞻基趋近床边,金忠费力地试图起身,却无能为力,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劳太孙惦记,只是老夫如今实在无法起身行礼了。”
朱瞻基安抚道:“金大人不必如此客气,我能坐在这太孙之位,全靠您当年在先皇面前的举荐,该行礼的应是我才对。”
朱瞻基提及的是永乐九年的事,确如他所说,朱瞻基得以成为太孙,实因金忠向朱棣的推荐。
不然的话,朱瞻基或许至今仍是皇长孙,别小看了这两个称呼的区别。
实际上,长孙即便再得宠,也不过是个臣子;而太孙则是未来的储君,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金忠闻言展颜一笑,他早对这位太孙殿下另眼相看,绝非仅因其嫡长孙的身份。
缓了缓,金忠开口问道:“太孙可知我召你前来所为何事?”
朱瞻基觉得这老头像是在托付后事,他不喜欢这种气氛,便未作答,转而说道:
“我已经让太医院的崔御医在此随时待命,兵部事务则交给杨士奇。
您只管安心休养,待病情好转,兵部还需您继续操持。”
“杨士奇啊。”
金忠点头赞许,“此人心思细密,虽出身布衣却能跻身翰林,才华出众,朝中皆知。
加之他曾任职兵部,熟悉其中事务,将兵部交付于他甚为妥当,太孙日后更应对他委以重任。”
朱瞻基颔首认同,这种事他自然明白,毕竟三杨的才能经历史验证。
若不是他们英年早逝,自家那位大明战神般的儿子,怕是未必能完成土木堡之变这样的大事。
毕竟除了土木堡之变,那三位辅政期间,他还打了三场大胜的北伐。
而这三次北伐,恰好都在三人辅政之时,等到最后一位去世不到两年,便是土木堡之变了。
将土木堡之变前后的局势稍作对照,便能见出三杨的才能。
金忠点评完杨士奇,稍作休憩,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册奏疏,呈递给朱瞻基说道:
“前些日子,我看太孙殿下用兵方略多显粗糙,思虑之后,遂拟此折,恳请陛下允准太孙殿下招募与殿下同龄之人组建一支专属护卫军,借此历练殿下之军事才能。
只可惜……”
金忠说着摇头叹息道:“本欲亲自辅佐太孙殿下训导这支新军,但如今看来恐难成行。
不过太孙殿下切记,陛下乃马上得天下的典范,若要稳居太孙之位,即便兵法造诣不及陛下,也万不可对军务全然无知。”
“幼军啊?”
即便被委婉批评,朱瞻基听闻金忠提及幼军之事,仍点头应允。
历史上他自己确实曾有这样的军队,于是嘴角浮现笑意道:
“罢了,这主意倒是可行。
回头我会将你的折子上呈。
不过你这老家伙莫要懈怠,崔御医叮嘱过,你要安心调养,按时饮食,保你活到九十九。
我的幼军还要靠你呢!”
“呵呵!”
听到这话,金忠忍不住轻笑,缓了缓神才哭笑不得地说道:“看来殿下是铁了心不让我消停了!”
“那是当然!”
朱瞻基点头附和,随后贴近金忠耳边低语道:“金老头,早日康复,等你身体好转,我定送你一份厚礼!”
话音未落,朱瞻基已转身离去,只留金忠满腹疑惑地喃喃自语:
“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