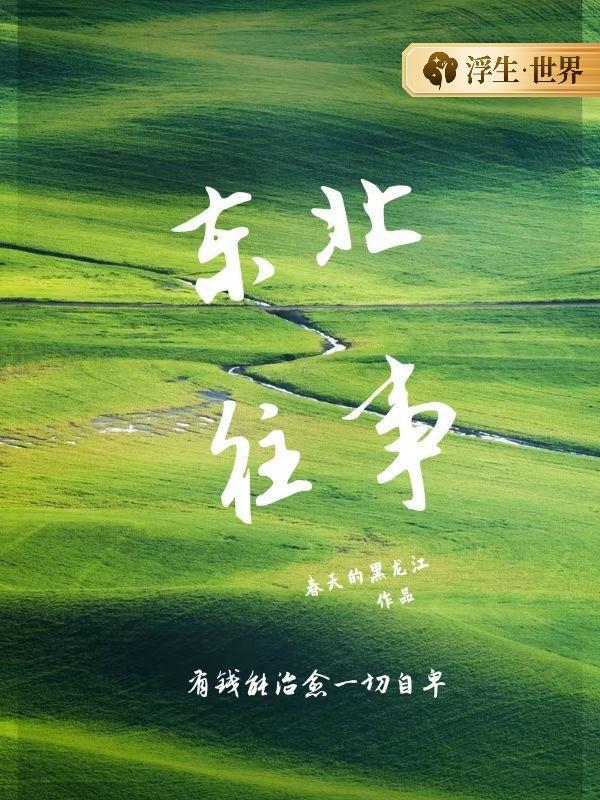布丁阅读>疼爱美强惨攻略笔趣阁 > 第75章 山中精怪 (第1页)
第75章 山中精怪 (第1页)
“……”
予濯一双黑眸沉凝,定定的看了眼前人好一会儿,看的眼眶隐隐发酸,才杯水车薪般伸手蹭了蹭阿尘的脸颊。
又烫,又湿,到底有多少眼泪才能流的满脸满脖子都是。
流泪的人无知无觉,平静的表情甚至未曾改变,可一滴一滴恍若化作万千悲鸣汹涌的翻滚着,填满予濯身体的每一寸,每一处。
他重重阖目,此时才发觉自己眼眶干涩的要命,像被尖刀划拉,搅弄,带着肉渣的红血一股又一股的倒流进体内,与悲鸣共振共存。
“啪嗒——”
予濯闻声眼睫轻颤,掀起眼皮,视线顺着阿尘摊开的指尖下移,落了一簇温暖的月光的床板下,一颗润白的珠子静静的躺在那儿,表面沾了点灰尘,很可惜的样子。
“不要了,我不要了,还给你。”
阿尘还维持着扔甜豆的姿势,纤长的五指在月下白皙到透明,他低头似乎在看那颗小珠子,鸦色睫毛在他脸上划出一道冰冷的上挑弧,淡色的唇微抿,继续说。
“我要、我要回去了,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说完,阿尘便再度挣扎起来。这次,更剧烈,更凶狠,宛若山穷水尽的囚徒,用尽全力只为逃离独属于自己的无间炼狱。
纤毫毕现的动作,意图,似乎是主人竭力在与另一人划清界限,予濯只觉得被阿尘丢弃在地上,染上尘埃的不是甜豆,是自己一颗血淋淋的心脏,像是被一根烙红的钢棍横穿过胸腔,又狠狠地将体内的骨骼,血肉捣烂,压磨,疼的予濯深吸一口凉气。
完全自主,没有思考,予濯腾出一只手,捡起床板上的甜豆,不在意是否脏污的含进嘴里,紧接着扣住阿尘下巴,对着那还在嘀咕着要离开的,冰凉的唇亲了下去。
四瓣唇,寒冰一般严丝合缝的紧贴在一起,其中一方还在不断深入,呼吸紊乱,温度却在不断攀升,白珠子被两截舌尖推来推去,不一会儿,便沾满了晶莹津液。
阿尘被迫扬起头,半眯的眸子一片水光迷离,像个即将溺水的人,双手紧紧抓着触手可及的衣料,予濯半坐在床边,一手圈禁着细瘦的腰肢,另一只手则搭在怀里人的后颈,施了点微微的力道,缓之又缓的揉捏,抚摸,带着不知多少的爱恋疼惜。
明明只分别了不到九天,这一吻却恍如隔世,嘴里都是奶甜味,予濯确实不喜欢,可这一刻,他却上瘾般一遍又一遍的从阿尘嘴里汲取,很甜,也很苦。
两人的吮吸,一颗甜豆很快便了无踪影,怀里的可怜人也没了乱动的力气,只能紧绷着身子,接受予濯的操纵,抗拒的被抬起下巴,与已经变得温热的唇厮磨。
予濯吻的很专注,看的更专注,他低垂着眼,萦绕在舌尖的字音一个一个被吐出,声音仿佛是撕扯着嗓子里的皮肉挤出来的,沉底嘶哑:“不要什么?”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丢掉?”
“这么些天,你那小脑袋瓜就想出了这么个烂结果来?”
含着很轻很轻的怒气,但这对于予濯来说,已经很不同寻常了,自从他母亲死后,他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情感。
不知是异常甜腻缠绵的吻,还是予濯失了态的质问,阿尘无声的抵抗倏而消失,硬挺的肩头溃败般塌软,这个人如一片零落的花瓣,混杂着冷风,彻底倒进了予濯怀中。
他双手死紧死紧的攥住予濯衣衫,攥的指尖发白,生疼也不松懈半分,压抑了不知多久的哭声终于被尽数释放。
他像个迷了路,又奇迹般归家的幼童,躺在自己最爱的人怀里,崩溃的,无力的哇哇大哭。
哭的很大声,很大声,似乎要将前半生受过的苦,咽下的罪一齐哭干,哭尽。
边哭,边埋怨:“你走了不告诉我,我——嗝——什么都不知道——”
“哪里都找不到,找不到,只能等你,可是——可是——”
“我也等不到——!!呜呃——!”
予濯掩去眼底苦涩,唇一下一下点在阿尘脸上,一颗一颗吻去晶莹的泪珠。
哭的半点没有刚才平静的样子。
阿尘发泄的时间并不久,声音很快就小了下去,他偏头躲过予濯为他擦拭泪水的唇角,一边抽泣着一边一头埋进他的胸膛中,左蹭右蹭,将脸庞蹭了个干净。
阿尘有了点往常的模样,予濯淤塞凝滞的胸腔终于得到了一缕新鲜空气。
指尖轻揉着阿尘的发丝,一缕缕细软的长发耷拉在予濯手中,像极了它正低落难受的主人。予濯指尖对着捻了捻,感受到上面浓浓的凉意。
他走后,阿尘大概每夜都来,床板上,被子上没有半点灰尘,予濯拉过床里的被子,给阿尘裹上,期间这人安静的不像话,予濯托起脸看,才发现人已经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
太晚了,他也太累了。
将人好好放进床里,予濯拿了旁边的油灯点燃,抬脚正要往外走,但一股巨力蓦的从衣角处传来,脚下一顿,他转身回望,却发现刚才还眯着眼的人正目光暗沉的看着自己。
“……”
予濯想张口解释,却被阿尘抢先:“你、要去哪?”
“不会走很远,只是去烧水。”
阿尘半信半疑的收回手,予濯不动声色的观察了下他,随即就走到床前,单手连人带被抱了起来。
“嗯——?!”
阿尘清瘦,骨架也纤细,可他不矮,被这样一抱,坐在予濯的臂弯里,晃荡间只能卷曲长腿,弯着上半身,双臂搂着予濯的肩背脖颈来定住自己。
予濯侧头睨了眼被吓的眼睛睁的大大的阿尘,眼底闪过几丝浅淡的笑意:“抱稳了,带你一起去。”
得带着啊,不然他可不想待会儿一转脸就看到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扒拉着门框朝里看自己。
阿尘把下巴搁在予濯肩头,声音小小的“唔”了一声,夹杂着些许困倦,算是回应。
猫儿一样,予濯轻笑一下,端着油灯继续往外走。
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刚才声音细微,懒洋洋的人却悄无声息的睁开眼,他低头,轻嗅了下眼前的衣料,唇角即刻勾起了一抹餍足阴郁的弧度。
哭红的眼眶,被吻红的唇,阿尘笑的好似阴谋得逞的山中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