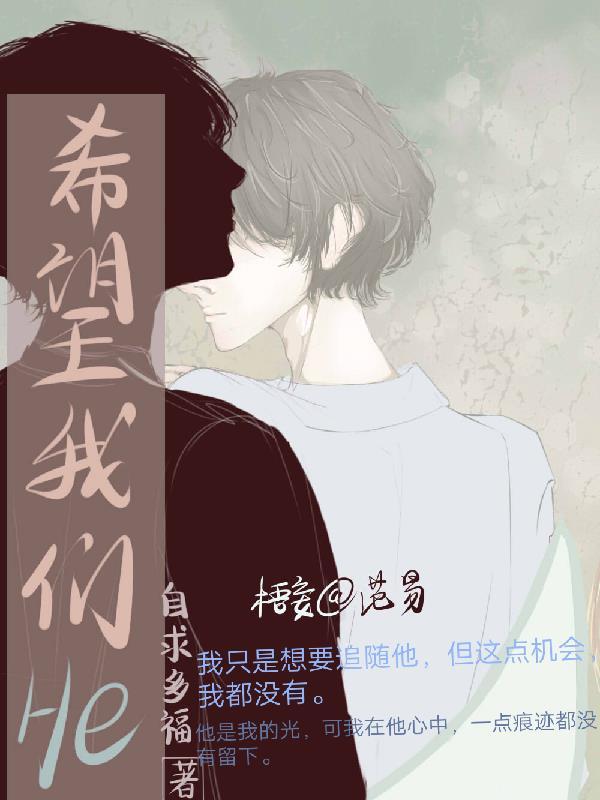布丁阅读>疼爱美强惨攻略笔趣阁 > 第49章 大概是个傻子 (第1页)
第49章 大概是个傻子 (第1页)
“……”
尽管予濯习惯喜怒不形于色,但他的眉心还是不经意往中间聚拢了一下。
寡夫?情郎?
他听不懂。
予濯生于乱世,活于末世,在那个朝生暮死,危机四伏,强者为尊的时代,血缘并不能换来庇护,住得近也不代表处的好,伦理关系被彻底销毁,因此雄踞一方,都是被人攀附,拍马屁的予濯费了许多力气,间或有大白鹅的帮忙,才大致熟悉了这个小村落古老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简单地缘关系。
但当题目超纲时,努力学习的尖子生也会不可避免的打迟钝。
予濯站在原地默不作声,暗暗观察周围人群闪烁变化的神色,有可惜,有同情,更有嘲讽与轻蔑。
所以,寡妇与情郎,大概不是什么好事。
心下有了决断,予濯就将手里半响动一下的羊羔递给站在一旁的金孟虎,又卸了身后的竹筐,这才走近去看。
扎作一团的人见了也让开了条小道,不过看那眼神,倒不是他们多识趣,更像是想看乐子。
密密麻麻的人群潮水般向两旁撤,里面的不太复杂的情状用眼一扫就能看出个清晰明了——只蹲着一个人。
距离三步远的地方,予濯停下,细细观察了一番蹲在自家门前的人。
这人静静的蹲在一角,瘦小的身子缩成一团,那颗脏兮兮的脑袋上的黑发像蓬草一般,有几根直楞楞的,直冲天际。
予濯盯着那几根冲天发,在心里默默点头,不认识。
他腿长个高,夕阳在他身后,往前方铺了一层阴影。
那人似有所觉,环住自己的手臂一动,脑袋猛地抬起,像被光线刺到一般,整个人瑟缩了下,纤长的眼睫颤动,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
刚从深山回来,路陡崎岖,不好走,也费力气,闷热流汗不可避免,予濯把领口松了,袖子挽到手肘,于是滚动的喉结,修长结实的手臂都露了出来,余晖小麦色镀上了一层金黄,像是裹了蜜糖的栗子,甜腻又软滑。
然后,予濯就见那抬了头的人瞪着一双上挑的大眼,似乎吞咽了一下,才站起身,朝自己走来。
站定到自己面前后,他仰着一张乌黑的小脸,细声细气,声音嘶哑的说:“你,我,亲、嘴。”
说完,他似乎还不满意的皱了皱细眉,又开口:“伸,舌、头。”
这一两句话听进了予濯耳朵里,也让围在附近的春雨村人听了个明明白白,一时间,有相互挑眉挤眼的,有管不住嘴的就迫不及待的交头接耳。
“哎呀呀呀!!!不知羞,合该去浸猪笼!”
“本以为他是个老实硬干的,没想到啊,啧啧啧——”
“幸而你家姑娘还没定,不然给了这予什么,可要受一辈子气啊!”
“没脸没皮的晦气东西,我呸!成天勾搭男人,是床上缺了男人睡不着?”
你一句我一句,说话的人多了,声音也就上来了,予濯本不想管,但说的多了,还不好听,自然叫人厌烦。
他转身,目光有点冷的看了过去,一群嘀咕的人被抓了个先行,因着畏惧身形高挑的汉子,都讪讪的冲予濯笑了笑,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大概是想把热闹看到底。
予濯怎么可能不懂:“各位还有事?”
他五官立体深邃,肤色较深,脸色一旦冷下来,就有种冷峻的慑人感,不经吓的人当即一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