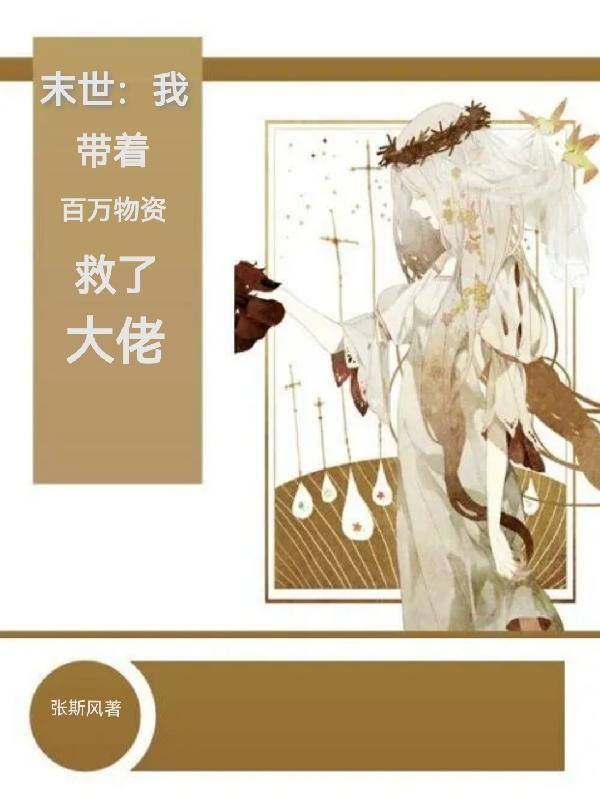布丁阅读>他的玩偶 > Chapter38(第2页)
Chapter38(第2页)
尤安眉目明朗,脸上的笑意真的好像恢复到了课堂上尤安教授的模样,温煦款款,儒雅和睦。
他突然侧着身子靠近:“找个乐子,你怕什麽?”
布兰温怔了怔,又听见他说,“跟我来。”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尤安上句话该怎麽回答,手腕上一紧,尤安握住他的手腕一拉。
布兰温没有甩开的时间,顺着尤安的力道往前一倾,下一秒,像是拉开门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老旧昏暗的单身公寓突然变成了明亮华贵的客厅。
而他重心不稳,额头撞在了尤安的胸口上,因为距离足够近,他再次嗅闻到那熟悉的玫瑰干花的味道。
这花香,透着久远时间烘出来的味道,配合着大厅明晃闪亮的灯光,音乐声和人群声,布兰温一时觉得有些晕眩。
尤安看出他有点不对,握着他的肩膀後退一步,问:“怎麽了?”
布兰温挣开他的手:“没事。”他转头看向周边,一时愣住:“这……这是哪里?”
他们刚刚不是还在……屋子门口。
“斯尔兰家族三年一度的盛会。”
什麽?
布兰温也是这时发现,他们站在宽大会厅的正中央,穿着华美礼服的女人和一身正装的男人从面前经过,却好像根本看不见他们。
此刻人群都在往一个方向看去。
那是一个半人高的台子,上面空荡荡的,只在中心摆放了一架钢琴。
支起的钢琴盖上灯光流转,後面有个穿燕尾礼服,头发用发胶固定的男子正在弹琴,指尖飞速起跃,钢琴音时块时慢地流淌出来。
不少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去。
布兰温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警局见过的那个安德里的哥哥。
他们的长相有部分相似,却又不尽相同。
布兰温还是不放心,侧头看了眼正在专心致志看钢琴表演的尤安:“我们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尤安却是低头看了看两人之间的脚尖,再打量打量两个人身体之间的距离。
他道:“反正我是不会,你嘛”他又嘶了一声,“不太好说。离我近点就没事。”
闻言,饶是布兰温再不相信他的规划,还是心存了他万一说的是真话的怀疑,只好往尤安的身边靠近一步。
尤安的嘴角彻底绷不住了,弧度是前所未有的大。
但他也没敢太嚣张,长眉微挑,兀自收了笑,盯着台上的人道:“这个人叫达加,是斯尔兰家族唯一的长子。那个安德里,不过是这个家族最见不得光的私生子,斯尔兰家族的産业恐怕不会让一个私生子继承。”
达加一曲奏毕,从矮凳上起身,优雅而高贵地向台下衆人行了一个贵族礼。
片刻,响雷般的掌声涌动。
“走吧,我们去楼上看看。”
尤安说完刚一动,布兰温就紧紧地跟着他。想到刚才自己说过的话,“你可以捏着我的衣角,用不着走路也挨得这麽近。”
布兰温真的有一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犹豫着,只见尤安转身就要走了,他赶紧继续伸手,攥住了他那件黑色西装侧边的衣角。
手心攥上那块衣角的时候,布兰温的身体僵硬了片刻,有些窘迫和难堪。
这情形令他莫名想到了曾经福利院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拉着他的衣角撒娇的样子。
他愈发的沉默不语,只是脚步有些乱。
二楼尽头的房间里,玻璃杯摔在地上碎成一片。
有个浑厚苍老的声音怒气高振:“安德里那些事情竟然是你做的,这些年我以为你学会安分守己,把不该有的心思都收拢好,没想到你变本加厉,演技学得真是精湛。我真的不知道对你母亲的亡灵该说些什麽?”
地上,碎玻璃渣滚到安德里的膝盖边,他跪在地上一直垂着头,听见後半句话终于擡头:“说什麽?你以为她很愿意听你跟她说什麽吗?她一个人病死的时候,你去看过她一眼吗?她从来就不稀罕你说什麽?”
桌子被拍了一下,连空气都在震颤:“不孝子,我是养了个白眼狼。”
“这是斯尔兰现任家族继承人,希威霍利。”尤安走到真丝软垫的沙发上坐下,长腿叠着,好像他才是这里的主人。
“不坐吗?”尤安擡头看着站在身边的布兰温,他捏着衣角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松开,闻言,他摇了一下头,转而继续看面前争执的两人。
“达加才是你的儿子,我不过是你养的一条狗,招招手就过来,挥挥手就滚开。你从来没想过要对我母亲说什麽,我也不祈求你能说些什麽。父亲大人,你向来雷厉风行,决事果断,一年前可以毫不留情地将我送走,那麽今天我做了什麽事又跟你有什麽关系呢?如果非要说血缘的话,我想你只要愿意花钱出去找找,不管儿子女儿你都会找到一堆。”
“你丶你!”希威霍利两鬓霜白,因为气急,胡须连着眉毛都在抖动,这次他直接扔了桌面上的一本书砸在安德里的头上。
安德里身形如山,结结实实被砸出了血,顺着额角脸颊留下一条骇人的血痕,他不惊不慌,反倒一只手捡起书,举起来,“还不过气,那就再扔一次。”
希威霍利这次气得直接抄起了手边的拐杖,就要甩出去的时候堪堪停住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痛心疾首,缓了会儿,他坐下,也放下手中的拐杖。
“你果然是长大了,还记得你以前总是很怕生人,畏首畏尾,我就常常不经意地把你往前推,同样是我的孩子,但你和你大哥完全不同,你更会看人眼色,洞察周遭,小心翼翼的。也许是我太忙太心急,可不管你再怎麽胡闹,也不能将自己的恶意施加在别人身上。人心都是肉长的,你难道一点心都没有吗?”
安德里卷着袖角擦了擦脸上的血迹,“不,你错了,我和大哥还是有相同地方的,你以为他就是个什麽好东西了吗?”
安德里从地上悠哉地站起来,不再管额角上的伤:“父亲大人,你一辈子在名利场上争斗,不管遇到什麽样的对手,鲜少有败绩。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你偏偏就要败在你的两个儿子手上,真是人生难两全啊。”
他长笑一声,在父亲落寞的目光中扶着墙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