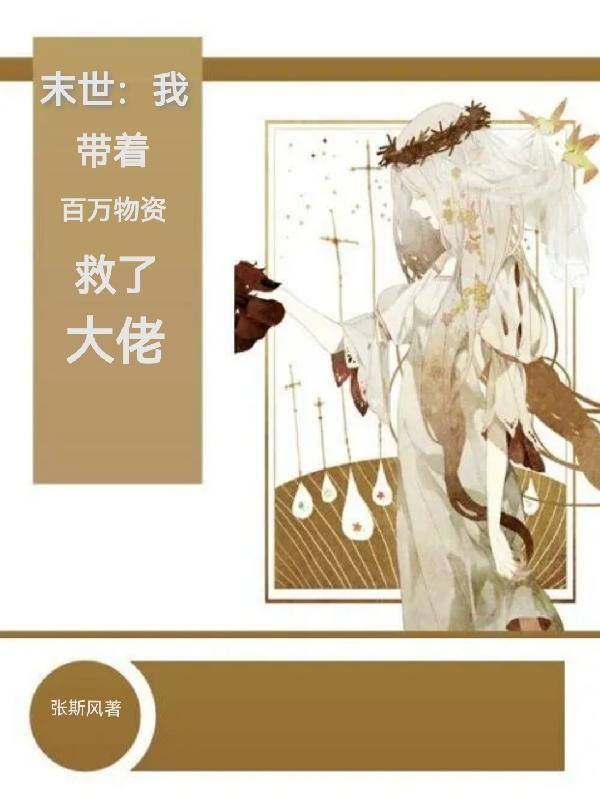布丁阅读>握爪微博 > 第44章 43 相拥(第2页)
第44章 43 相拥(第2页)
梦里的荒诞事挥之不去,现实里惹出事的坏蛋还要像抱娃娃一样把他抱在怀里。
他懊恼地去掰江革的手,纹丝不动。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难道只是因为和江革睡在一张床上就做春梦了?他的自制力就这么差?
沈不予一往前挪,江革就立马粘过来,他都快挪到床沿了,江革还是死死地抱着他。
混乱之中,他忽然听到一阵极轻的梦呓。
“小鱼。”江革低哑叫他,“。。。。。。小鱼。”
沈不予一怔,随即心脏砰砰狂跳起来。
他回不了头,只能僵硬地听着江革一遍遍地叫自己,一声一声,像无意识的低语又似惆怅的叹息。
如果现在有面镜子摆在沈不予面前,他的脸色一定是红得快要滴血。
沈不予闭上眼,在自己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硬生生把那些旖旎思绪给逼退了才重新闭上眼。
一夜无眠。
第二天沈不予起得比树上的鸟还早。昨天后半夜一个晚上没睡着,精神还是亢奋。
不敢闭眼,怕做的还是扰人心神的梦。
他出去把后院的盆栽全部打理了一遍,买了早饭回来,洗了个澡才觉得浑身舒服了一点。
7点是江革起来的点,沈不予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竟然还是不见他起床。
沈不予站在房门前,想起昨天的事,男子汉大丈夫反倒扭捏起来了。
他暗自做了一会儿心里工作才慢慢拧开把手,结果刚进去就愣在原地。
昏暗的房间里,江革已经醒了,坐在床上呆滞地偏头看着窗帘,脸上有隐约的泪痕。
笼罩在男人身上的悲伤和阴霾如有实质,让站在门口的沈不予再也不能踏进一步。
听到开门的响声,江革转头看过来。
还有眼泪无声地从他眼眶里划出,眼神却和瞳色一样冰冷,还未来得及收起的恨意和绝望倾泻而出,扼上沈不予的喉咙。
那道熟悉的与世隔绝的茧又裹在江革周围,没有人能靠近。
只是茧里的人游离世外,也会因为七情六欲被困在这里像个小孩子一样掉眼泪吗?
沈不予喉头滞涩:“江革,你怎么了?”
江革垂下眼,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半晌道:“。。。。。。没事。”
一个夜晚,同床异梦。
江革也做了一个梦。
和沈不予混乱旖旎的梦不同,他又梦到了曾经在斗犬场经常梦见的小路,行走在罪孽和无尽黑暗之间,这次路边多了一具斗犬的尸体。
獒吉死不瞑目,尸体上是骇人的伤口,瞪圆浑浊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重塑人身的江革。
想要继续往前走,他就必须从獒吉的尸体上跨过去。
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如行尸走肉一般踩在尸体淌出的鲜血上。
道路的尽头仍旧是一扇门。
只是这次门内不再是模糊不清的了,他从里面看到了大雪下巍峨的雪山,山体每一根凌厉的线条都是他所思所想的模样。
一只修长干净的手从门内伸出,自他愣神之际将他拉进门内,看到了一个在大雪下洁白的小人,浑身上下发出暖融融的好闻气味。
小人把他拉进怀里,被这股气息包裹的感觉像回到母体羊水般令人舒适。
失而复得的狂喜让江革的呼吸急促起来,紧紧抱住小人。
只是小人很快就消失了,徒留他留在鹅毛大雪中。
茫茫雪原上空无一物,世界忽然只剩下了他自己。
接下来的梦痛苦而混乱,江革已经记不清梦中一闪而过的几幕是什么内容了,只记得他在雪原上长途跋涉,只为寻找一人。
时间在他身上不曾流逝,但却在腐蚀他的记忆。
他恐慌,恐慌那人在他的记忆慢慢消失,憎恨那人不声不响地离开。
冥冥之中有声音告诉他小人已经永远消失了。
贪痴嗔念如千斤之鼎束缚在他深陷冰雪的四肢上,茫然四顾,他已经快要遗忘小人留下的气息,似乎从始至终只有他一个人。
这是何其的不公平。
作者有话说:
*出自泰戈尔《园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