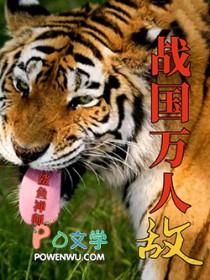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石上青松处洁清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清丽流郁的乐音泻于指尖,飞英落,瑶瑾歇,只听得鸾凤吟徽,玄云垂泣。
曲未毕,人已癡,t萧瑶不住拭泪,吟道,“将乘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阮姑娘的这一曲《别鹤操》真是闻者落泪,见者伤悲。”[1]
阮如玉手抱焦尾,怡然一礼,“别鹤操,伤别鹤,红颜青冢遥相送,不堪白首断肠人,世人大多以为此曲不吉,殊不知曲中情义足以感天地,惊鬼神,公主殿下能听懂此曲,想来也是知琴懂琴之人了。”
萧瑶向她招了招手,示意她走近些,“本公主虽然并无心仪之人,却也能听出阮姑娘在这首曲子中寄予的肺腑真情。”她似是叹了一口气,“说来也是可惜,太子那麽好的一个人,怎麽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江北,要不然姑娘与太子当真是一段佳话。”
韩笙闻言,连忙拉住萧瑶的手,“殿下慎言。”
萧瑶嘲弄一笑,拂开韩笙的手,不屑道,“怕什麽,本公主又没说假话,谁做了亏心事谁自己知道,既然敢做,难道还怕别人说不成?”
其实萧瑶从前同萧景衍并无什麽交情,她说这话,完全是目睹了贾太后在后宫中的胡作非为,心生不满,再如何说,贾太后也是她父皇名义上的妻子,却在她父皇死后大张旗鼓地搜集面首,这让她这个女儿如何能看得下去。
韩笙不敢再听下去,随便找了个由头便告退了。
阮如玉见韩笙走了,正色道,“公主殿下相信先太子是枉死的吗?”
萧瑶默了默,才说,“人都已经死了,信与不信,又有何用?阮姑娘,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好自珍重,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缅怀。”
阮如玉环顾四周,看见还有几名婢女在侧,便道,“殿下可否让她们离得稍远些,臣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请,想要亲口禀告殿下。”
萧瑶见她神情郑重,便一扬手,“你们都先退下吧。”
婢女们垂首称是,纷纷往外挪了几步。
“有什麽话就说吧。”
阮如玉跪下行了一礼。
“你这是做什麽?”
“臣女所言兹事体大,还请公主殿下恕臣女无罪,臣女才敢说。”
萧瑶微微蹙眉,“行,你说吧,本公主恕你无罪。”
阮如玉擡头看着萧瑶的眼睛,声音极轻极缓,“殿下方才说,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好自珍重,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缅怀。”
“是啊,本公主说的不对吗?”
“那如果,这个人是先帝呢?”
萧瑶明显怔了一下,她的脸上渐渐浮现出震惊的表情,她不敢置信地凝视着阮如玉,“你说什麽?你再说一遍。”
阮如玉面不改色,徐徐道,“公主殿下可还记得,先帝是怎麽死的,又是死于何时何地?”
“父皇……”萧瑶的身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我不知道。”
萧瑶的确不知道,先帝死时,她还年幼,只听说宫里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贾太后——也就是彼时的贾夫人下令封锁禁苑,消息不得外传。
萧瑶连她父皇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就看到了漫天飘扬的白幡,还有宫人们哭红了的眼睛,她的父皇就这麽死了,死在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
萧瑶当时哭得厉害,跟着发了一场高烧,等她再醒来的时候,就听说了皇兄萧寰继位的消息,而她身边的婢女居然都换了一批,她哭着闹着说要找原来的婢女,却被告知宫里闹了鬼,见过鬼的婢女都被贾太后下旨殉葬了。
从前,萧瑶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妥,可被阮如玉这麽一说,她也不由得起了疑心。
虽然她的父皇当时年事已高,但并没有什麽大病,一向将养得很好,可自从贾惜柔进宫侍奉,她父皇的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最后竟然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她父皇从病发到死亡不足一个时辰,这不是太蹊跷了吗。
“阮姑娘,你都知道什麽?”
“臣女不敢欺瞒殿下,臣女其实并不知道先帝之死的究竟,臣女方才所言,不过是自己的猜测罢了,先帝的死和随之的死一样,像是一个扑朔的谜团。”
萧瑶若有所思,“你为什麽要同本公主说这些?你可知,如果本公主将这些话禀告母后,你会是什麽下场?母后虽然并非我的生身母亲,可她待我一向不错,阮姑娘,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
阮如玉非但不惊慌,反而还轻声笑了一下。
“你笑什麽?”
“公主殿下,臣女方才好像并没有提及太后娘娘半个字,不知殿下是如何想到太后娘娘身上的?”
萧瑶一怔……好像还真是欸……
“这就说明,其实公主殿下对于先帝的死一直也是心存怀疑的,所以,臣女方才一说,殿下就不自觉地想到了太后娘娘。”
“你还真是敢说。”萧瑶稍一欠身,微笑道,“阮姑娘,你真不怕我回头把你给卖了?”
“臣女不怕。”
萧瑶挑眉,“为什麽?你可不要说什麽相信本公主的为人,我这个人,最是我行我素的,那些奉承话对本公主都不好使。”
阮如玉娓娓道来,“高山流水,难遇知音,公主殿下能听出我的心中所想,是为知己,所以我愿意相信殿下。”
萧瑶闻言,默不作声。
阮如玉继续说道,“伤别鹤者,不止男女之情,亦有血亲之谊,臣女听说先帝在世时对公主殿下疼爱有加,公主难道就不想为自己的父皇查明真相吗?”
萧瑶似乎被她的话触动了,她蹙眉思索,指尖上的鲛绡帕转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