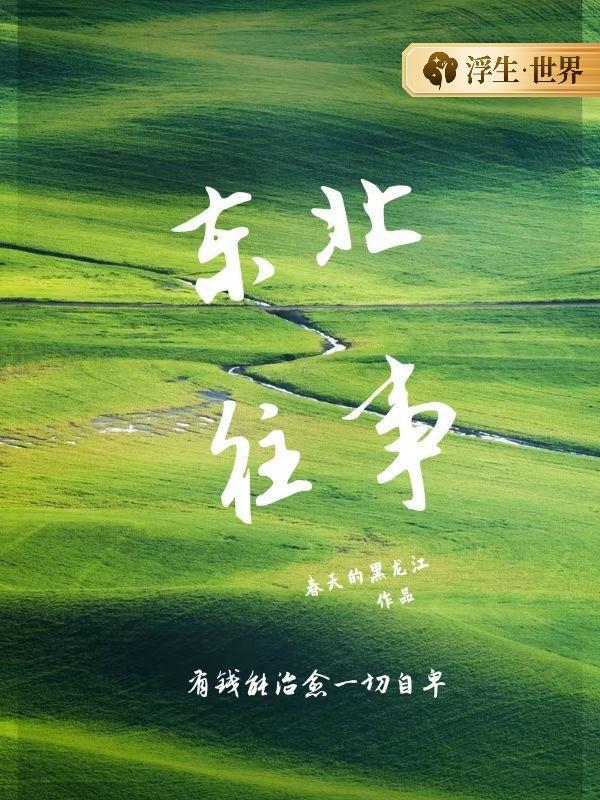布丁阅读>我见卿卿多妩 > 第八章 出气(第2页)
第八章 出气(第2页)
叶雍淳一方的骑手立刻卷起青色旋风,马蹄铁在夯土地面划出火星,朱漆球再次升空,赵弘鄞的乌木杆与许良谟的弯头杆绞作一处,闷响震痛手心。
赵弘鄞阴冷地注视着他,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道:“我早提醒过你……”
许良谟咬了咬牙,勒紧缰绳便要退开,乌木杆头却追着马球,不偏不倚砸向他的右臂,动作快得像毒蛇吐信——
铁器撞击皮甲,他自马鞍上重重坠落,银鳞护腕撞上地面,大宛马前蹄高高扬起,精准落在他的左肩!
飞溅的尘沙混着鲜血泼向彩旗木栅,许良谟身弓如虾,痛苦地捂住碎裂的肩骨。
“一时不妨,失手了。许公子不会介怀吧?”赵弘鄞居高临下,神情倨傲地道歉。
许良谟目眦欲裂,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自然。小公爷只是无心之失。”
接二连三出事,这马球赛已然不能进行了,简王紧皱着眉头过来,瞧着凄惨的许良谟,一副不忍直视的神情。
“哎呀,你说说,这是怎么弄的!”他连连感慨,又忙不迭吩咐小厮,“快,把许家小子扶到后头院子去,再请个太医来瞧瞧。”
小厮忙将许良谟搀扶起来,扶着他往校场后头供达官贵人休息的房舍去。
“你啊!”简王指了指赵弘鄞,“横冲直撞的,合该小心些!”
赵弘鄞羞愧地低下头。
“罢罢罢,”简王长叹一声,“本王今日就不该来,还是打道回府消遣吧!胜负也没分,这扳指索性给了许家小子,做个补偿好了。”说着径自取下扳指,交给陪同的国子监官员,随即负手离开了。
也不知是真没瞧出猫腻,还是只当眼不见为净。
赵弘鄞恭敬地拱手相送,待简王出了大门,他这才站直身,朝面面相觑的其余众人拱了拱手,道一句失陪,旋即朝看台上那道瘦弱荏苒的身影大步走去。
他刚刚踏进凉棚,绍桢已然急不可耐地低呼起来:“赵、赵二哥,你疯了吗?这么明目张胆对他动手,傻子都瞧得出来!”
赵弘鄞倒是神态自若不见悔意,一面在她面前蹲下一面淡淡道:“早想收拾他了。”取过桌上放着的小瓷瓶,挽起她的裤腿开始给她上药,“我替你出口恶气,不好吗?”
冰凉的药膏涂抹在青紫的膝盖上,不知什么成分,效果立竿见影,张绍桢疼得瑟缩了一下,抓紧桌角倒吸一口凉气:“你……你实在不必为我做到这种地步,反倒连累你。”
他动作一顿,抬头看了她一眼:“绍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但我是很喜欢你的。你若真认我这个朋友,就再也别说这种话。”
张绍桢很少在他脸上看到如此认真的神情,不由呼吸一窒,下意识往后退了几分。
赵弘鄞不以为意,低头继续为她上药,和缓道:“许良谟小肚鸡肠,叶雍淳同他一丘之貉,你年纪还小,不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道理,可不能被他给骗了,一点小恩小惠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你又不是没朋友,不缺这一个,你说呢?”
他已经上好了药,大手握着椅子的扶手,将她圈在椅子中,那双漆黑深邃的眼眸凝视着她,张绍桢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赵弘鄞笑了笑,松开若有似无的禁锢:“这我就放心了。”
这时,邓池行色匆匆地从看台后绕了上来,草草行了个礼,顾不得赵弘鄞还在场便急切道:“四少爷,家里来贵客了,您快去瞧瞧吧!”
绍桢精神一振,忙不迭从椅子上起身:“不好让贵客久等,赵二哥你担待,我这便回去了。”
赵弘鄞倒是没阻止,笑着点头。
她顾不得膝盖疼痛,快步迈出凉棚,待走远些才透了口气,夸赞邓池:“不错,近日有长进,都知道看脸色,给少爷我打圆场了。”
邓池张圆了嘴:“……四少爷您说什么呢?东宫殿下回京了,接您进宫的内臣现就在青禾堂候着呢!”
“什么?!”
凉棚中的赵弘鄞耳力极好,忽然眉梢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