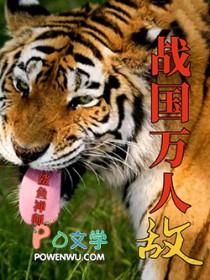布丁阅读>补天裂辛弃疾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但是不说出来会替你不甘心啊。你明知他不是你的弟弟,却还对他那么好。你为他耗着命,年如一日。最少、最少也要让他知道,你对他——
“烟姿——”祭司要喝止已然是不及。那向来干脆利落的女神宫,已经把话说了出来。
听到祭司的声音,怔了一怔,侧头看去,夏树脸色阴沉,一声不吭。
“其实有时候不是每次请昭神灵都会有所昭示的……”她说的也是事实,只不过,在此时,毫无说服力而已。又想想,她下了决心开口。“其实我也有——彻世需要的东西——”
她从袖中拉出一角白布,布料柔软而冰凉,上面溅染着斑驳血迹,时间应该已经久远,血迹已是淡淡的褐色,像是开败的残梅,零落着。
那是一箭射下来的,而后在加冕的夜里,在她再次牵着他的手回去时,顺着他的指尖流到她的手指上,再染了她袖间里的一角白袍。还记得当时的血还是温暖的,在夜色下不显,他人却始终是微微笑着,辉着夜色。温暖如光,也温暖如血。只是到今昔,那光消了,那血凉了,无声的沉寂。
他只是拿她当孩子。记得当初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好凶的小女神官——让她常常看着水镜中倒影出神就是半天——自己真的好凶么?她从各族送来的女子间,挑出她自己所喜欢的,不顾他的反对,任性地送到他身边去。就好像自己陪在他身边一样,他遣回去,自己再带回来。才不管,那些女子是否愿意。有什么不愿意的?他的人,本是极好的——
这样一番小女孩家心事,
只剩了这一片袍角,可以纪念着。也要为了夏树用了吧。毕竟他也是你最关心疼爱的弟弟。虽是如此想,在心里还是幽幽地叹了口气,拿在手里看了半晌才递出来。
夏树默不出声的接过去,握在手里,柔软得感觉不到任何生命。
“你想好了?”祭司还是再次的问,毕竟彻世不比昭命,彻世的结果多半是——倒不如永远不要去明白。虽然辉夜之前就曾细细地安排过,若是他不在了,还请好好的看护着——他留下来的重要的人,为他做任何他所需要的事。而这末来的君王所要求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彻世。想要看明白些什么?
我不会后悔的。
半晌,终于还是下了决心,沉默着点了头。
祭司看他如此,也不好多说,和烟姿相视一眼,后者的眼里是一片的赞同,这小女神宫,大概不是那么清楚彻世的后果
吧,只是想知道些,再知道些,他过去的事,再无人知的事。
启开了水镜。整个空间开始慢慢地透彻,隔开了外界。彻世的水镜慢慢地从地下浮现出来。和一般用来占卜的水镜是不同的,它更大,更透彻,更真实。如同一片平静的大湖,映在脚下,轻泛着微波,像是思念,轻柔的持念着,曾经珍爱的人,在乎的事,曾经的过去。真实的传递着,让那一份悲哀也更加的真实。
一方袍角缓缓融了进去,镜面得了那一丝血痕,开始静微而欢悦的动荡起来。慢慢地昭显出他所想看到的东西。
就算是有了王者的血,而且合了两个祭司的幻力,那片水镜,却仍然看不太清楚,就像是恶楚,隔了一层纱。然则已经够了,已经够夏树明白很多事,父王,母后,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为自己做过的事,所有他从来不曾在意的事,点点滴滴。只是些微片段。模糊不清。但是已经能够让他明白,真正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悲哀的事实,真实的事实。
布由上的血痕在很快在水镜中淡淡的散去。水镜也慢慢的平复,悄失,只是短短的片刻之间。只剩下那一份衣角,静静的落在地上,原本斑驳如残梅的血色退去,只剩下一片苍白色,静恒的显失着失落。
只需要那么短的时间,却宛若千年大梦,但该明白的,已经全都明白。
只是迟了,不是迟了水镜中的千年一瞬,而是迟了生生世世。
迟的是那一刀,终还是扎了下去。竟还是扎了下去。从他手中,自以为是义无反顾的扎了下去,在那般惊惧疑虑的目光中,缓缓的刺得更深些,听着他的宛如梦呓,夏树?
而自己竟然没有好好看上他一眼,听上他一句。最后只剩得那一声,既惊而疑,如忧如悲。夏树?
夏树?
从今后,再没有人会那般亲切的为他,唤他——夏树。
原本就是将死之人,可是怎么死是不一样的——死在他的手上。那不是错,是罪。
“你看到些什么?”烟姿看他不出声,出不了声。终于忍不住问。彻世是只能给一人看的真实,就算他们也同在镜中,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可是她还是出于私心的想要知道,夏树究竟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关于他的事。
夏树神色惨变,一言不发。看着烟姿有三分惋惜的小心翼翼把那一方衣角拾在手中。突然一把夺了过来。
他去弱水,他去了弱水。弱水——是死后才会去的地方。死后才会去。可他去了弱水。哥。
哥。
那个人带他走过春秋,穿越着年华,抬眼就可以看到的淡静的笑,细心的教诲,温柔的呵护——
可如今,都去了弱水。
再顾不得和烟姿、祭司说话,夏树便从大殿中冲出来。再顾不得先前事事算无遗漏的安排,针对着他的安排——顾不得说词,顾不得泄漏,顾不得权衡,顾不得之前苦心竭虑的种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