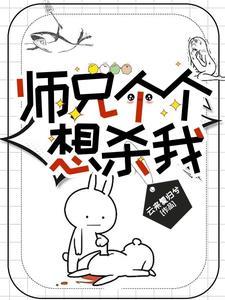布丁阅读>韭菜花致癌 > 第101章 青楼女(第2页)
第101章 青楼女(第2页)
"别看。"
温热的液体却从指缝渗进来,混着血腥气和脂粉香。
等再睁开眼时,游廊的青砖上留着道暗红的拖痕,像条僵死的蜈蚣。
---
春杏蘸着桂花油给韭菜花梳头时,铜镜里映出个尖下巴的美人。
珍珠粉把菜色的皮肤养成了羊脂玉,唯有眼底两片青影怎么也遮不住
——自打上个月目睹翠云被活活打死,她夜夜都从血淋淋的噩梦里惊醒。
"今儿是你十五岁生辰。"
柳三娘的声音裹着蜜糖似的从门外飘进来,大红织金马面裙扫过门槛,
"牡丹啊,妈妈给你备了份大礼。"
韭菜花盯着妆奁匣里那支金步摇,凤凰嘴里衔着的红宝石像要滴下血来。
春杏给她绾的手突然抖,簪头戳疼了头皮。
廊下传来杂沓脚步声,龟公们正在前厅挂红绸灯笼。
"今晚要开红倌。"
柳三娘捏起她的下巴左右端详,
"城南米铺的赵老爷、盐运司的王书办都递了帖子。"
染着蔻丹的指甲划过她脖颈,
"你可得给我挣个满堂彩。"
暮色四合时,前厅飘来酒肉香气。
韭菜花穿着茜红肚兜坐在雕花拔步床上,腕上金镯叮当乱响。
春杏临走前往她手心塞了颗蜡丸:
"含着这个,能少疼些。"
窗纸渐渐透出灯笼的猩红色,像浸在血水里的月亮。
门轴吱呀一声,酒气混着汗臭扑面而来。
穿宝蓝绸衫的胖子踉跄着扑到床前,腰间玉佩砸在脚踏上碎成两半。
"五十两!老子花五十两睡个雏儿!"
酒糟鼻凑到她颈窝乱拱,韭菜花死死咬住蜡丸,尝到满嘴薄荷的凉。
锦帐金钩晃得人眼晕。
胖子撕开她中衣时,后腰的肥肉在烛光下泛着油光。
韭菜花盯着帐顶绣的鸳鸯,突然想起村口那条总冲她摇尾巴的大黄狗。
去年腊月它被剥了皮炖肉时,眼睛也是这么湿漉漉地睁着。
剧痛袭来时她咬破了舌尖。
血顺着嘴角流到枕上,和胖子胳膊上抓出的血痕混在一起。
男人喘着粗气在她耳边笑: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小浪蹄子还挺野。"
床架吱嘎声里,窗外飘来零碎的琵琶调,弹的竟是《孟姜女哭长城》。
五更梆子响时,柳三娘带着婆子来验元帕。
猩红的绸布展开在晨光里,老婆子啧啧两声:
"是个烈性子,抓得客人满臂血痕。"
柳三娘却笑弯了眼:
"好!这样的才招人疼。"
转身从锦盒里取出对翡翠耳坠,
"今晚起正式挂牌,名号就叫红胭脂马。"
韭菜花蜷在染血的被褥里,听见春杏在廊下挨打。
柳三娘的骂声尖得像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