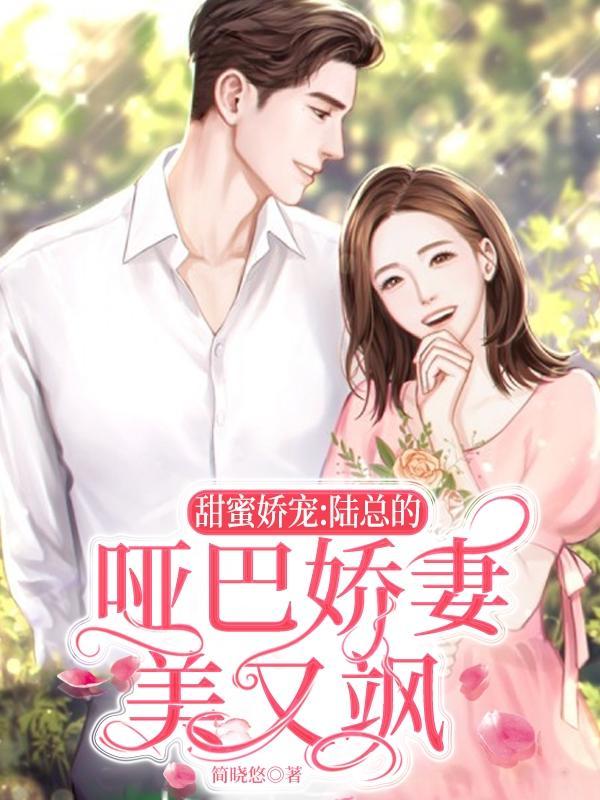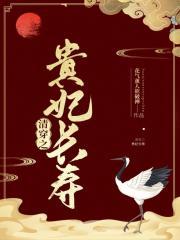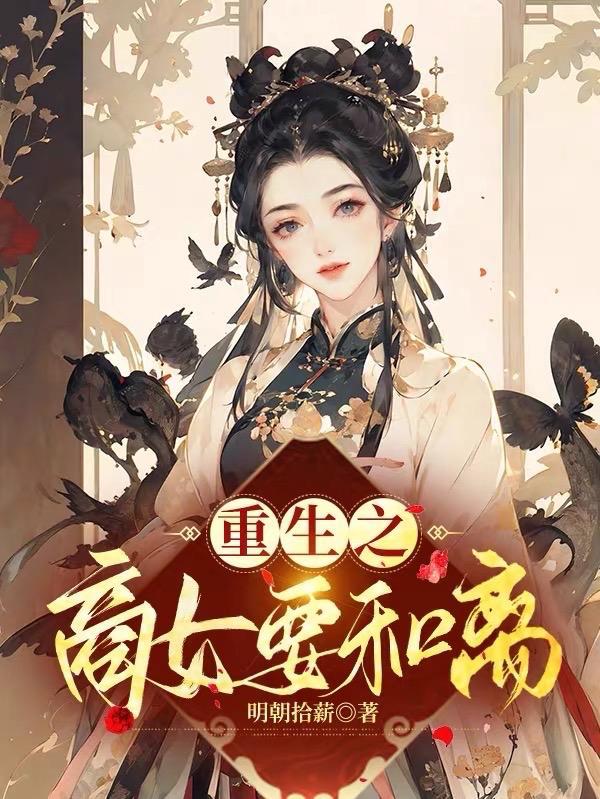布丁阅读>姐姐让我们做吧 > 第224章 用心险恶(第1页)
第224章 用心险恶(第1页)
会试将至,士子们越用功。
读书寮里,每日灯火通明,学子们连饭都顾不上吃。
王守生刚从读书寮回来,一脸感慨:“有个读书人疯了。”
虞苏正歪在软榻上,闻言,捧着话本的手微微一顿,“疯了?”
“哎呀,魔怔了。整日念书,茶饭不思,最后撑不住,昨夜大吼大叫,说自己若不中便跳河,吓得同僚连夜写信寄回他老家,估摸着不久他的家人就要来接回去了。”
虞苏叹了口气,摇头道:“科举不易,读书读到这般,倒是可惜了。”
这年头,科举几乎是寒门学子的唯一出路。
为了出人头地,他们不知道付出多少努力。
可这条路,不仅仅是靠努力,天赋更重要。
清北的学生是老师教出来的吗?
虞苏认为,他们固然受到了良师的引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他们自身底子好。
她合上书册,偏头吩咐:“也是个可怜人,叫下面好生照顾。另外让厨房多熬些汤,送去给他们补补。就当是读书寮的福利。”
王守生连声应下,心道县主是个好心肠的。
青葵在旁听着,笑道:“小姐这般用心?说不定读书寮日后真能出个状元呢?”
虞苏闻言,也笑了笑:“若真出了状元,那咱们读书寮,岂不是名声大振?”
转眼,会试的日子到了。
贡院门外,被围得水泄不通,好生热闹。
这三年一次的会试,不光是士子拼命的战场,也是世家贵女们暗暗观望的时候。
谁才是今年的金榜之才?谁又是未来的朝廷栋梁?
虞苏原本没打算来,可拗不过秋实的念叨。
“小姐,听说贡院旁边有家包子铺,老板做的包子特别新鲜好吃……”
于是,她就带着人过来了。
三人围坐在一张小木桌。
虞苏点了两笼,没多久,包子就上了。
一掀开,蒸笼就冒出腾腾的白雾,空气中都是鲜肉汤汁的香气。
秋实早已两眼放光,双手捧着热腾腾的包子,小口吹着气,一边吃一边咕哝:“会试一旦通过,便能进殿试,听说陛下会亲自点榜,他们说探花不一定是最有才的,但一定是最好看的。”
虞苏一边听,一边随手拿了个包子,轻轻咬了一口,赞同点头,“是有这么个说法,探花郎向来多是风采出众之人。”
秋实扫了一圈,嘟囔着:“我都看半天了,怎么没见几个长得俊的?”
青葵忍不住笑了,揶揄道:“你这丫头,怕不是眼光太高?探花郎总得才貌双全,哪能满大街都是?”
几人嬉笑做一团,却听一旁几桌食客也在谈论。
“今年高手不少啊!听说有几个寒门出身的才子,文章极好,许是要金榜题名了!”
“谁说不是?听闻冬试的榜,就是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也不知这会儿定亲了没有?”
“没有,听说有人上门提亲了,可那人说考完再说,分明是胸有成竹。真是羡煞我等呀!”
虞苏听得有趣,忍不住轻笑一声。
婚姻也是一种投资。
有些人家,眼光毒得很。
科举放榜前,就挑个潜力股,提前定亲,把人预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