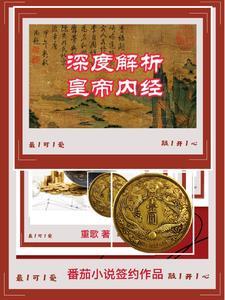布丁阅读>狼夫啸月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嗯?狼王疑惑地审视着她,他对茗月的话半信半疑,儿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却从来没怕过他,可此时此刻,他从茗月的脸上看到的是惊惶和畏怕。
他看穿了茗月的小心思,知道她在说谎,以此来挣脱他。
在狼王还只是个狼孩的时候,他将小茗月视作自己的主人,无条件听命于她。
可现在的他不一样了,他不再是当初那个弱小无助的狼孩,他威猛霸气的狼王,而他将茗月当作自己的狼后,那是他的女人,他碰她怎么了?
狼王的手腕蓦地垂下,然后缓缓探入她的腰间,他感觉到茗月的身子在紧绷中颤抖,脊椎骨僵硬着靠在柳树干上。
他低头附在茗月的耳根旁,说:“孤答应让你回家,孤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你也必须要顺从孤一次,好吗?月儿。”
“不要~”茗月呜咽恳求着他。
可狼王却说:“月儿,别怕,就像山洞里的那夜一样放松即可,孤又不会伤害你。”
“那一夜?”
茗月脑海中闪过当时昏睡中做过的那场羞于启齿的梦,可那是她的梦境而已,为何狼王却知道?
“你忘记了吗?那夜的你可不是这般抗拒的呢!”
狼王将头凑到她的颈间,火热的鼻息烫红了她的脖颈,那一抹红晕从胸前晕染至耳后根,红扑扑的两颊像是涂满了胭脂粉似的,微启的唇珠娇嫩似水,让人忍不住亲上去。
“你说什么?那天你该不会对我……”
茗月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她记得自己醒过来时明明身上的衣裳都是完整如初,怎么可能那样了呢?
狼王见她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那羞涩的表情甚是惹人喜爱,他故意骗了她,他邪魅笑道:“没错,可是你太甜,孤还没吃够。”
话音落下之时,温热的唇瓣覆了上去,她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禁锢住她。
“呜呜呜~”
茗月闭眼啜泣着,衣裳仿若凋落的花瓣一层一层被褪下,他蛮横地撬开她紧闭的牙关,唇舌交织在一起。
他贪恋着那股清甜,肆无忌惮地啃咬着她薄软的唇瓣,每咬一下,她的身子便颤抖一下。
挣扎的茗月被他困住手脚,动弹不得,她无力地挣扎几下便放弃了,眼眶里淌出一行酸涩委屈的泪。
泪水润过唇角刺激着他的味蕾,狼王怔了证,停下了动作,睁眼看向身下的人儿。
此时的茗月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她睁开泪眼,用祈求的眼神望着他,啜泣之下的肩膀微微抖动着。
他瞥见了茗月左肩上那条触目惊心的伤痕,虽已愈合,可那条瘢痕却像只大蜈蚣爬在她肩上。
狼王蓦然起身,转过身去,而衣衫不整的茗月则蜷缩着身子,双手护胸,埋头哭泣。
他不知为何,每当茗月悲伤落泪时,他便会不忍心疼,仿佛她的眼泪是某种术法,且对他百试百中。
狼王指着丛林一方,“那里便是下山的方向,待天亮后,孤就送你下山。”
她没有答话,仍旧低声啜泣。
“穿好衣裳,夜里风大,别着凉了。”
茗月正在慢慢平复不安的情绪,她缓缓坐起身来,将地上的衣物一件一件披在身上,尽管衣料已经被撕扯得破破烂烂。
归心似箭的她等不及天亮,整理好衣物之后,便自顾自的起身朝山下走去。
她一声不吭,片语不说,就连个眼神都不愿投给他,看来是对刚才的事记恨上了。
狼王虽然答应放她下山,但却担心着她的安危,于是,他和之前一样默默地跟在远处。
茗月察觉到身后的脚步声,即便是不回头也知道是他又跟了过来。
她站住脚步,转身对着远处的狼王喊道:“你别跟过来!”
茗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而且是用那种绝望的恳求语气对他喊着。
他无奈叹息,只好转身往回走,清冷的月光照亮着他落寞的背影,直至背影消失在丛林深处,茗月才放心地继续下山。
情绪平定下来后,她决定还是得回山匪营寨打开那个铁匣子,她知道翡翠玉佩很有可能不在里边,但即便是希望渺茫,她也想试试找找。
这一次她学聪明了,她在营寨废墟中找到山匪用的利斧,利斧对她来说太过沉重,两只手抬起来也甚是费劲。
茗月使劲挥舞着斧头朝铁匣子上的锁砍去,然后前几次不是砍了个空,就是砍中箱体,那把锁依旧完好无损。
她歇了几许,继续砍了数下才将那锁砍断。
铁匣子被她打开的那一瞬间,她闻到一股焦烟味,不禁呛咳几声。
待焦味散尽过后,她才伸手进去探物。
咱要不直接给她做了?
茗月将铁匣子的东西悉数倾倒在地,借着幽暗的月光,她才看清那都是些珠宝碎银,根本没见着那枚翡翠玉佩。
她愈发失落起来,遗失阿母的遗物令她自责不已,委屈和自责的泪水滴落在焦黑的铁匣子上。
找不到阿母的翡翠玉佩,又不想待在这鬼地方,她抹了抹泪,朝着山脚下走去。
困意与饿意席卷而来,她的身体已经累到无力,双腿发软,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
莫说此时已是深更半夜,没有光亮的山路尤为难走,就算是大白天,想要徒步数十里路回长安城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此时此刻的茗月已经身心俱疲,全靠意志撑着。
来到山脚下那处当初遭遇山匪之地,她站在路中央四处眺望着,凭借模糊的记忆来确定回长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