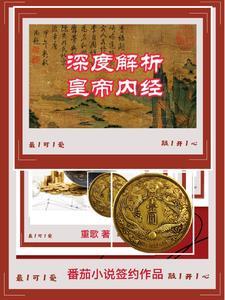布丁阅读>虫族之兄长的遗产 > 第84章(第1页)
第84章(第1页)
“不可以。”郝誉眯起眼,发觉床上崽什么都没穿,幽暗被窝里是一段雪白中带点殷红色的身体。他狠狠挥舞拳头,要打又不知道打哪里,威胁道:“还想被打屁股吗?”
“都要被打烂了。”白岁安一把抱住枕头,察觉自己回到郝誉的安全区后,继续肆无忌惮蹦跶起来,“小叔。我屁股手感好吗?”
“……”
“不好。你干嘛打那么多下。”白岁安别过脸,小声抱怨道:“小叔都不打修克。啊~我知道小叔会给修克做软开测试,那也很刺激嘛。”
郝誉微笑,一巴掌把崽按在枕头里,按得他呜呜乱叫,喘不上气才松开。再抬头,白岁安头发都乱成一团,一撮撮到处乱飞。
“小叔,你是不是急了。”
郝誉抬头,认真思考,“我在思考,怎么操练你。”
“……怎么操练修克,就怎么操练我吧。”白岁安要求道:“小叔是故意打我屁股吗?”
“嗯。”
“为什么。”
郝誉道:“打烂屁股,你就没办法偷偷训练了。”
“我才不相信。”白岁安更嘀咕起来。他还想继续说什么,郝誉已起身走向门口,留下几句寒暄后离开。白宣良与其擦肩而过,得到一管皮肉伤特效药,兴致勃勃拿来给孩子用。
不料,白岁安对药不在乎。比起什么时候好起来,他更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在文化、战术、实战上全面压制修克。
“雌父。帮我把桌上三本书全拿来吧。”白岁安打个哈欠,一顿体力劳动后,他终于感觉到疲倦,脸埋在枕头上昏沉沉发声,“我再看一会儿书。”
白宣良不敢打扰他,帮忙上完药后,转到前面赫然发现孩子陷入熟睡。
毕竟是孩子。
白宣良纯良地想着,抽走白岁安正在看的几页书,悄悄退出房间,“郝誉为什么要打芋芋呢?”白宣良来到厨房,看向户外被郝誉揪出来泄愤的修克,压下询问的心思,专心处理食材。
户外。
修克得知不用作业,蝎尾就没有停下来过。郝誉每扫过去,都能看见那根灵活蝎尾上下打转、绕圈打转、比划心心打转……总之就是各种打转。转得郝誉都腾出三秒思考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这么外露的开心时刻。
不记得了。
郝誉进军雄养育中心上得第一课就是管理自己的心态和身体。自那之后,郝誉除了见哥哥总破功外,一直很克制,高兴也不尽兴,时刻提防敌人出现。
如此想想,郝誉看修克那快活似小狗的尾巴怎么看都不爽。
他上前一把揪住修克乱来的尾巴,不等孩子反应,强行拽着来到训练场。修克短促叫几声发现没效果后,眼巴巴跟着郝誉,就怕自己的尾巴被拽疼了。
到目的地,松开蝎尾。郝誉严肃道:“有学到什么吗?”
修克:“啊?”
拽尾巴?学到什么吗?修克转过身,摸摸屁股,察觉这样有些太愚蠢后,绷紧脸,严肃思考起来,“感觉蝎尾很不舒服……嗯。屁股也会疼。然后。那个。然后。”
居然能学到东西吗?
拽蝎尾居然是教学之一吗?
修克开始啃指头,眼珠乱转,“不应该不想写作业?”
郝誉忽然怀念白岁安举一反三的能力。他承认白岁安叛逆期非常不好管教,肉眼可见喜欢挑战自己的道德底线。但作为一个学生,白岁安能给老师带来最大的成就感。
不然,大家怎么都爱教聪明学生呢?
“第一课,管理好自己身体每一个部分。”郝誉用脚踢下身边一个大麻袋。这是军雌临走前留下的“教学道具”,郝誉嫌太多,让他们直接丢在训练场。他道:“雄虫孵化虫蛋,破壳的雌虫幼崽到一定年龄,家里都会寻找同虫种长辈帮忙进行教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修克没想过。
因为他恰恰好没有被同虫种的长辈教养过。他是各种意义上的私生子,雌父也非蝎族,身边没有可靠的大人,蝎尾也是懵懵懂懂用着,到上学才被老师教育不能成天晃尾巴。
他并没有经历过同虫种教养,也无法理解同虫种教养背后的意义。
“……我。”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郝誉宽容道:“没什么好丢脸的。你才十九岁,可以慢慢学。”
“虫族大类繁多,小类数不胜数。每一个虫种在结构与基因上都有细微差别,了解身体,应用身体,有同虫种长辈带领会更方便,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蝎族和其他虫种最大的区别就是蝎尾。”
郝誉露出自己的蝎尾。其他蝎族雄虫不常用蝎尾,已趋于大流将身体部分遮掩起来——郝誉大概是厮杀管了,他管什么大流主流,杀个血流成河!黑峻峻的蝎尾像另外长了一双眼睛,鳞甲上两处枪弹般的凹槽,闪烁白光。
日光毒辣。
修克已被注视到汗毛直立。他下意识后退一步,脚下却不知何时被郝誉的蝎尾纠缠住,向后摔个屁股蹲。
“了解自己的身体,学会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才是实战的基本功。”
郝誉双手抱胸,任由自己的蝎尾缠紧修克的小腿,沿着腿肉向上,狠狠把孩子拽到自己眼皮下。
“你看,到了这个地步。你的蝎尾在做什么呢?”郝誉摸摸下巴,抬脚轻踩下修克焉巴巴的蝎尾,奚落道:“我好像听到它在哭。嗯……修克?”
修克确实要哭了。
和寻常冰冷的鳞甲不同,虽面上和郝誉一样冷冰冰,缝隙里却无一不彰显个事实:军雄今天火气很大。